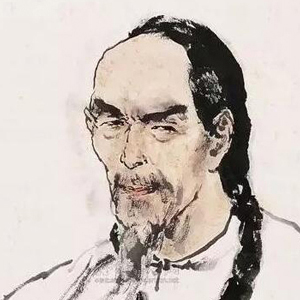通常认为这首词为伤春之作。惜春伤春是历代词的传统题材,留下的佳篇汗牛充栋,僧挥的这首《金明池》即为其一,被选编进《宋词三百首》。全词基调哀婉,上片主描景,下片主抒情,行文多有绮语;而作者又为僧人,词作别有一种情趣。
“天阔云高,溪横水远,晚日寒生轻晕”,上片首句一气连用了三个境界开阔的短句,一反伤春词细腻入文的模式,起笔突崛。三个远景,如果只从单个分开细看,纯粹只显豪阔苍远的境界,于伤春主题并不切合,但一经组合排列,哀氛就透过词句四处弥漫,奠定了全词“伤”的基调。起笔突崛而又不显唐突、违拗,且自有新意,正是这首词入文的妙处。
“闲阶静、杨花渐少,朱生掩、莺声犹嫩”,这是近景,与首句远近结合,成一画境。首句奠定了词意的气氛基调,但并不能判断句中所描绘的是什么时间季节,这第二句作者点明了是暮春时节。“闲阶静,杨花少,朱生掩”,是目之所及的视觉感受,莺声嫩则为听觉感受,这几个“冷色调”意象的有机叠砌,予人幽深、凄切的感觉。然而,作者并未让这些意象营造的感觉如滔滔江水一放到底,一览无遗,而是且放且收,“莺声犹嫩”,一个“犹”字,恰如其分地把前头的表达“收”了起来。但不是单为了收而收,是为了接下去能更好地放。虽然莺声“犹”嫩,但也不能再“嫩”很长日子了。
“悔匆匆、过却清明,旋占得馀芳,已成幽恨”,此句既是前面景的描绘后的情的流露,也是“莺声犹嫩”收了之后的续放。时光易流,一过了清明,各种各样的花儿,就都陆续委地凋谢了,丛中和枝头只疏疏落落地留了一点儿残英。到这时,莺声已老,不再嫩了;可见“犹”得短暂、无奈。“却几日阴沉,连宵慵困,起来韶华都尽”,这句是接前句的深延。几天前还有若有若无的遗留的花儿,可忽忽几日,稍没注意,一下子就只剩满目绿肥,些许瘦红也难觅了。
上片主描景,景中时也露情,下片主抒情,全为伤春心事。“怨入双眉闲斗损,乍品得情怀,看承全近”,写的是春愁怨情。怨入双眉,思量甚苦,皆因春去无情。“深深态、无非自许,厌厌意、终羞人问”,写的是怨态,情动于衷而形于表。因春去而心怨,因心怨而神形缱绻。“深深态”两句是女子自怜自爱、自怨自艾的情态,大有美人惜春迟暮之感。“深深态”和“厌厌意”二词运用对比,将女子愁绪满怀的怨态和因春去精神萎靡的无力之状形象描写出来,读之令人感同身受,心怀大动。 [4]
末句“纵留得莺花,东风不住,也则眼前愁闷”是全词最堪回味处。心怨源于春逝,这里却说即使莺声和花香留住了,仍还是愁绪难遣。原来春去仅是引子,最伤心处,并非春天美景消逝,而是时间老去人老去——春天可以再来,人却难以再少。无言之伤,尽在其中矣。
此首伤春之词,却出自诗僧笔下,可见其性情坦荡,不拘礼法。上片阶静生掩,美人春睡。杨花渐少,莺声犹嫩,正是暮春景象。睡起方识春色已阑,幽恨遂油然而生。下片因惜眷而自怜,因伤春而厌厌。这首词把年轻女子的多情与娇羞写得十分动人,她有些慵懒,有些感伤,有些哀怨,也有些甜蜜。一个感情真挚、热烈而又羞涩矜持的女性形象跃然于纸上。 [1] [5]
有观点认为下阕以“怨入双眉闲斗损”句过片,承上阕末意,也补足了人对春光去尽的反映。一“闲”字、一“损”字,暗暗透露作者对这种伤春怨情的保留态度。以下渐渐转出真意:先用“乍品得”二句过渡,语极委婉。这两句真像耐心布道者的口吻。“深深态”二句,又忽作狮子吼,将悔憾怨恨种种情怀之实质一语道破:自我期许太多,就难免不深深作态;羞于向人吐露,才必定会恹恹不振。“怎知道”以下又如佛手指点迷津。从正反两面说去:想闻得好“音信”,关键在于“忘了余香”,不必有所留恋,这是从正面说;若总想“留得莺花”,执迷不悟,那只会招来“愁闷”,自堕苦海,这是从反面说。禅理而能入词,又说得如此有诗趣、理趣,实属不易。
这是许浑在宣城送别友人后写的一首诗。这首诗前后两联分别由两个不同时间和色调的场景组成。前联以青山红叶的明丽景色反衬别绪,后联以风雨凄其的黯淡景色正衬离情,笔法富于变化。而一、三两句分别点出舟发与人远,二、四两句纯用景物烘托渲染,则又异中有同,使全篇在变化中显出统一。
“劳歌一曲解行舟”句写友人乘舟离去。古代有唱歌送行的习俗。“劳歌”,原本指在劳劳亭(旧址在今南京市南面,也是一个著名的送别之地)送客时唱的歌,后来遂成为送别歌的代称。劳歌一曲,缆解舟行,从送别者眼中写出一种匆遽而无奈的情景气氛。
“红叶青山水急流”句写友人乘舟出发后所见江上景色。时值深秋,两岸青山,霜林尽染,满目红叶丹枫,映衬着一江碧绿的秋水,显得色彩格外鲜艳。这明丽之景乍看似与别离之情不大协调,实际上前者恰恰是对后者的有力反衬。景色越美,越显出欢聚的可恋,别离的难堪,大好秋光反倒成为添愁增恨的因素了。江淹《别赋》说:“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借美好的春色反衬别离之悲,与此同一机杼。这也正是王夫之所揭示的:“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姜斋诗话》)的艺术辩证法。
这一句并没有直接写到友人的行舟。但通过“水急流”的刻画,舟行的迅疾读者可以想见,诗人目送行舟穿行于夹岸青山红叶的江面上的情景也生动地表现了出来。“急”字暗透出送行者“流水何太急”的心理状态,也使整个诗句所表现的意境带有一点逼仄忧伤、骚屑不宁的意味。这和诗人当时那种并不和谐安闲的心境是相一致的。
“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句则是表明诗的前后联之间有一个较长的时间间隔。朋友乘舟走远后,诗人并没有离开送别的谢亭,而是在原地小憩了一会。别前喝了点酒,微有醉意,朋友走后,心绪不佳,竟不胜酒力睡着了。一觉醒来,已是薄暮时分。天色变了,下起了雨,四望一片迷蒙。眼前的江面,两岸的青山红叶都已经笼罩在蒙蒙雨雾和沉沉暮色之中。而朋友的船,此刻更不知道随着急流驶到云山雾嶂之外的什么地方去了。暮色的苍茫黯淡,风雨的迷蒙凄清,酒醒后的朦胧,追忆别时情景所感到的怅惘空虚,使诗人此刻的情怀特别凄黯孤寂,感到无法承受这种环境气氛的包围,于是默默无言地独自从风雨笼罩的西楼上走了下来。(西楼即指送别的谢亭,古代诗词中“南浦”、“西楼”都常指送别之处。)
第三句极写别后酒醒的怅惘空寂,第四句却并不接着直抒离愁,而是宕开写景。但由于这景物所特具的凄黯迷茫色彩与诗人当时的心境正相契合,因此读者完全可以从中感受到诗人的萧瑟凄清情怀。这样借景寓情,以景结情,比起直抒别情的难堪来,不但更富含蕴,更有感染力,而且使结尾别具一种不言而神伤的情韵。
此诗主要表达了诗人送别友人时的惆怅。前二句以青山红叶的明丽景色反衬别绪,后二句以风雨凄凄的黯淡景色正衬离情,以描写景色作为反衬的手法表达情感,笔法富于变化。
这是一首叙事诗,在写作手法上相当朴实,记事、写景,较少抒情,语言工整,用词精确恰当。从文义的表面上看,赞美韦彪关心民间疾苦而祈神求雨,但本意是对韦中丞等州府官员愚昧迷信、劳民伤财行为的批评,对自己蒙屈而沦为下僚的悲叹。
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无神论者,他曾针对韩愈天有意志、能赏罚的观点,提出:“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他认为天地只是自然物,既无意志,也不能赏罚,“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天说》),希望天地能赏罚、有哀仁都是迷信(《天说》)。他还认为,“生植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祸乱,皆人也……其事各行不相预,而凶丰理乱出焉”(《答刘禹锡天论书》),天事与人事各不相干。另外,在《非国语》中,他还指 出:“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歇,是恶乎为我设?”认为天地、元气、山川等自然物的运动变化是自然而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根据这些认识,柳宗元对韦中丞黄溪祈雨的荒诞行为,必然是持批评态度的。
当时的永州刺史韦彪,跟柳宗元并没有什么深厚的交情。柳宗元到永州一年多后,唐宪宗改元大赦天下,韦彪便北移了。这人毫无才干,连北移的贺表也是请柳宗元写的。但由于他身为永州的行政首长,柳宗元的顶头上司,柳宗元又是待罪之人,并且希望得到朝庭的赦免和重新起用,因此柳宗元当然不便直接批评韦彪,只能用赞赏的表面形式来记述这件事。但诗题中标明“口号”,而“口号”是古人随口吟成的诗体,这便给诗添了几许诙谐。诗人写这场荒诞的祈神求雨戏时,字里行间充满了辛辣的讽刺,传神地刻画出了韦彪其人:兴师动众,不仅劳民伤财,而且是沽名钓誉的行径;神祠荒凉清冷,象征他的愚蠢糊涂;场面宏大,巫师装神弄鬼,讥讽他的迷信与无知;并且通过“惠风仍偃草”的写实,“灵雨会随车”的用典,以对比的手法来揭示韦彪祈雨的无功与荒谬。据诗人的《游黄溪记》记载,黄溪在城东七十里,“黄神”乃是王莽的后代,是避祸来的。韦彪导演的这场闹剧,吹吹打打弄了整整一夜,直到天亮才收场,使周围的百姓都受到了惊扰,根本不是在为老百姓祈福,而是在“造祸”,并且灾祸波及到了“骑客路”与“野人居”。
诗的最后两句,才是诗人真实意图的流露:自己是“俟罪非真吏”,却奉命随行,做太守的清客、帮闲,成为献媚取悦长官的低级僚属,这对胸怀大志的柳宗元来说,是非常羞愧的。如果他是有实职实权的地方官,定会珍惜手中的权力,尽情施展自己“以利安元元为务”的抱负,干一番兴利除弊的事业。
本诗是写上皇西巡绿由和剑阁天险。
安史叛军威胁都城长安,故有圣主西巡蜀道之事、“轻拂”,表明诗人态度,对圣主玄宗弃京西巡不以为然。
剑门,“《旧唐书》:剑州剑门县界大剑山,即梁山也,其北三十里有小剑山。大剑山有阁道三十里《一统志》:大剑山,在保宁府剑州北二十五里,蜀所恃为外门户。其山悄壁中断,两崖相嵌,如门之壁,如剑之植,故又名剑门山。”剑门高耸,崖石嶙啕,“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李白《蜀道难》),一入剑门安全可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