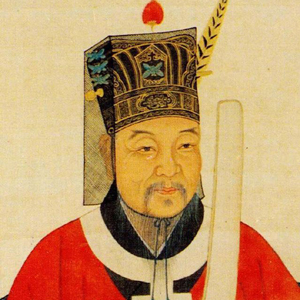夜空中的一轮圆月,惯会助人哀伤快乐。人们高兴时,那明月便洒下皎洁的柔辉,为人助兴、凑趣——“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李白《月下独酌》);人们忧伤时,那月色也顿时变得冷幽幽的,照得人倍感凄凉,令人难耐,——“明月,明月,照得离人愁绝”(冯延巳词)。
《苍悟谣》里的这位“离人”,叫明月照得失眠了,于是他苦恼极了,呼天而叹:“天!休使圆蟾照客眠!”(圆蟾,即圆月;传说月中有蟾蜍。)意思是说老天啊,不要再让这圆月照得这我离家的人睡不着觉了!这位他乡之客本来就满怀离愁别绪;何况月下独立,又怎能不思念“隔千里兮共明月”的那一位呢?
再说,如水月光,也容易使人毫无睡意,“明月皎皎照我床”,“牵牛织女遥相望”(曹丕《燕歌行》),这怎么能睡得着呢?而那月光,又偏爱照失眠人,这真是:“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晏殊《蝶恋花》)月圆之夜,本是亲人团聚之时。可是词人呢?却是月圆人未圆。难怪这位离人终于压抑不住,不得由仰天长叹了。可见,这句“天!休使圆蟾照客眠”。是经过一番千回百折的苦恼之后发出的百般无奈的叹息之词!
月光如练,然而人隔千里,这边是他乡仰望,那边是闺中独看。这位痴情人不禁异想天开了,说:月亮啊,据说你是一面宝镜,你能照出她的芳姿倩影吗?“人何在?桂影自婵娟!”他凝视着那轮明月,那嫦娥般美丽的身影在何处呢?只有桂影疏密有致,空自盘旋罢了。
此时此地,他可能情不自禁地想起他俩月下携手漫步的美好时光。然而此时呢?人却远隔千里,这多么令人愁怅啊!
这首小词通过对圆月观感,抒发出沉挚的思念之情。寥寥十六个字,然而曲折有致。这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梅尧臣语)的高妙描写手法,真可谓“以少胜多”了。
汉乐府里有《上邪》一曲,意思就是“天哪!”这首小词也采用这种咏叹手法,且全用口语述之,富有民谣色彩。这首小词在婉约词中,显得十分清新别致。
词的上片回忆过去“酒恋花迷”的生活。“伫立东风”写词人迎着东风,久久地站立,“东风”暗示了时令节气,说明此时正值春季。“南国”的春天本是美好的季节,词人却“断魂”南国,悲戚哀伤,默然凝伫。开篇两句便塑造了一个伤心欲绝的浪荡词客的形象。南国的春天勾起了他对过去美好生活的回忆:“花光媚、春醉琼楼,蟾彩迥,夜游香陌”这两个工整的对句,分别由景而情,以极凝练、含蓄的笔墨,浓缩了无数个良宵美景,无数次的纵游娼馆酒楼,沉湎于声色酒乐。而今忆及,当时“酒恋花迷”的生活,累煞多情的“词客”。
过片首句,以“别有”二字起,另辟一境,引出所怀之人。以下,“眼长腰搦”四字写出了她容貌的美丽和身姿的婷婷袅袅,“痛怜深惜”四字写出了两人真挚的情意和深深的爱恋,用语十分简练。接下来的“鸳会阻”两句,紧承上片,回到现实,由情及景,写傍晚时分,冷雨纷飞,愁云凝聚,天色一片青碧。由于“鸳会阻”、“锦书断”,词人眼中的景色也显得凄凉无比,与上片的“花光媚、春醉琼楼,蟾彩迥,夜游香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词作的最后,设想对方遇良辰当好景,也应苦苦思念自己:想别来,好景良时,也应相忆。”从对方写来,这是柳水怀人词常用的手法,由此亦可见柳永怀思之深。
刘熙载在《艺概·词曲概》中说:“‘酒恋花迷,役损词客。’余谓此等,只可名迷恋花酒之人,不足以称词人,词客当有雅量高致者也。”需要承认,这样的词句格调是不高,但其中也有诸多难言的苦衷。柳永遭黜落后,打着“奉旨填词”的招牌流连烟花巷阳,沉溺酒香舞影,风流放浪,冶游无度。 这一方面是他在发泄心中的不满,寻求精神的寄托;另一方面也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使然。有宋一代,自上而下狎妓成风。只是,柳永比其他人走得更远,更加坦率而无所顾忌。为官后,柳水收敛了许多,“又岂知,名宦拘检,年来减尽风情”(《长相思·画鼓喧街》)。但宦游的惨淡与辛酸,使他对人们趋之若鹜的功名利禄产生了厌倦,转而对自己曾经沉湎其中的世俗享乐又产生了心理上的认同:“图利禄,殆非长策。除是恁,点检笙歌,访寻罗绮消得”(《尾犯·晴烟幂幂》)。可见,“酒恋花迷”是柳永生活中的一抹亮色,是他在现实中找到平衡的一个支点。
“诗囚”句,元好问《放言》“韩非死孤愤,虞卿著穷愁,长沙一湘累,郊岛两诗囚”。诗囚,“为诗所囚”,指孟郊、贾岛作诗苦吟,讲求炼字铸句,把诗看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好像成为诗的囚徒一般。孟郊以穷愁为诗,至死不休,处高天厚地之大,而自我局限于穷苦之吟,真似一个诗中的累囚。“诗囚”二字,与“高天厚地”形成藐小与巨大的强烈对比,亦可见好问之别具匠心,造句用语新颖别致。“死不休”的夸饰手法,亦比“死方休”、“死即休”来得巧妙,勾勒穷愁不断,极深刻独到。
这首诗是评论孟郊的诗,元好问认为他根本不能与韩愈的诗相提并论。孟郊与韩愈同为中唐韩孟诗派的代表,但有不同。孟郊一生沉落下僚,贫寒凄苦,郁郁寡欢,受尽苦难生活的磨难,将毕生精力用于作诗,以苦吟而著称。孟郊的才力不及韩愈雄大,再加上沦落不遇的生活经历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视野,使得他的怪奇诗风偏向个人贫病饥寒,充满幽僻、清冷、苦涩意象,被称为“郊寒”。而韩愈的诗歌虽有怪奇意象,但却气势见长,磅礴雄大,豪放激越,酣畅淋漓。司空图说他“驱架气势,若掀雷挟电,奋腾于天地之间。”
韩愈的这种气势雄浑,天然化成的诗歌风格正是元好问所崇尚的,而孟郊的雕琢和险怪的风格正是元好问所批判的。因此,元好问认为孟郊和韩愈不能相提并论,韩愈的作品如江山万古长存,与孟郊比,一个如在百尺高楼,一个如在地下。不过,在诗中元好问对孟郊也有同情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