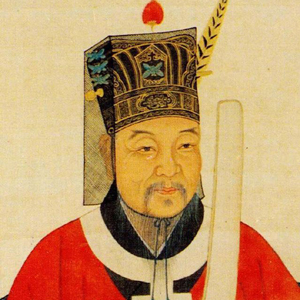这是一首托物言志的咏物诗,表面上歌颂橘树,实际是诗人对自己理想和人格的表白。全诗可分两部分,前十六句为第一部分,缘情咏物,重在描述橘树俊逸动人的外美,以描写为主;后半部分缘物抒情,转入对橘树内在精神的热情讴歌,以抒情为主。两部分各有侧重,而又互相勾连,融为一体。诗人以四言的形式,用拟人的手法塑造了橘树的美好形象,从各个侧面描绘和赞颂橘树,借以表达自己追求美好品质和理想的坚定意志。
第一部分重在描述橘树俊逸动人的外美。
开笔“后皇嘉树,橘徕服兮”等三句就不同凡响:一树坚挺的绿橘,突然升立在广袤的天地之间,它深深扎根于“南国”之土,任凭什么力量也无法使之迁徙。那凌空而立的意气,“受命不迁”的坚毅神采,顿令读者升起无限敬意。橘树是可敬的,同时又俊美可亲。
诗人接着以精工的笔致,勾勒它充满生机的纷披“绿叶”,晕染它雪花般蓬勃开放的“素荣”;它的层层枝叶间虽也长有“剡棘”,但那只是为了防范外来的侵害;它所贡献给世人的,却有“精色内白”,光采照人的无数“圆果”。屈原笔下的南国之橘,正是如此“纷緼宜修”,如此堪托大任。这节虽以描绘为主,但从字里行间,人们却可强烈地感受到,诗人对祖国“嘉树”的一派自豪、赞美之情。
此诗第二部分,即从对橘树的外美描绘,转入对它内在精神的热情讴歌。屈原在《离骚》中,曾以“羌无实而容长”(外表好看,却无美好的内质),表达过对“兰”“椒”(喻指执掌朝政的谗佞之臣)等辈“委其美而从俗”的鄙弃。橘树却不是如此。它年岁虽少,即已抱定了“独立不迁”的坚定志向;它长成以后,更是“横而不流”“淑离不淫”,表现出梗然坚挺的高风亮节;纵然面临百花“并谢”的岁暮,它也依然郁郁葱葱,决不肯向凛寒屈服。
诗中的“愿岁并谢,与长友兮”一句,乃是沟通“物我”的神来之笔:它在颂橘中突然揽入诗人自己,并愿与橘树长相为友,面对严峻的岁月,这便顿使傲霜斗雪的橘树形象,与遭谗被废、不改操守的屈原自己叠印在了一起。而后思接千载,以“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收结,全诗境界就一下得到了升华——在两位古今志士的遥相辉映中,前文所赞美的橘树精神,便全都流转、汇聚,成了身处逆境、不改操守的伟大志士精神之象征,而高高映印在历史天幕之上。
本诗借物抒志,以物写人,既沟通物我,又融汇古今,由此造出了清人林云铭所赞扬的“看来两段中句句是颂橘,句句不是颂橘,但见(屈)原与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镜花水月之妙”(《楚辞灯》)的奇特境界。从此以后,南国之橘便蕴含了志士仁人“独立不迁”、热爱祖国的丰富文化内涵,而永远为人们所歌咏和效法了。这一独特的贡献,仅属于屈原,所以宋刘辰翁又称屈原为千古“咏物之祖”。
此诗八章,每四句为一章。第一章以菅草和白茅相束起兴,映射夫妇之间相亲相爱正是人间常理。其中的菅草白华和茅草之白有象征纯洁与和谐的爱情意义,与《召南·野有死麕》中的“白茅包之”“白茅纯束”相参证,可见“白茅”在当时是一个常用的带有象征意义的意象。本来常理不言自明,可是这里偏偏是“之子之远,俾我独兮”。一正一反,奠定全诗凄婉哀伤的悲剧基调。
第二章以白云普降甘露滋润那些菅草和茅草,反兴丈夫违背常理,不能与妻子休戚与共。虽然从字面上看是白云甘露对菅草茅草的滋润与命运之神对被弃女主人公的不公平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对应和映射关系,但实际上看似怨天实为尤人,矛头所向实际是这不遵天理的负心丈夫。
诗的第三章以北流的滮池灌溉稻田,反向对应无情丈夫对妻子的薄情寡义。此章虽然在起兴方法上与前两章一样,以物喻人,以天道常理反兴人情乖戾,故郑笺解释曰:“池水之泽,浸润稻田使之生殖,喻王无恩于申后,滮池之不如也。”但是紧接着长歌当哭的女主人公话锋一转,由“之子”转向“硕人”。关于“硕人”,前人如孔颖达疏引王肃、孙毓说,以为硕人指申后,朱熹《诗集传》以为硕人指幽王。揆诸原诗,以下提及硕人的两章都以物不得其所为喻,暗指人所处位置不当。郑玄笺解“硕人”为“妖大之人,谓褒姒”,与诗意合。话锋既转,下一章的感叹就显得自然而贴切了。
第四章承前三章反兴之意,以桑薪不得其用,兴女主人公美德不被丈夫欣赏,反遭遗弃的命运。与自身命运相反,“维彼硕人”,想起那个“妖大之人”却媚惑丈夫取代了自己的位置,这一切实在是煎熬人心的事情。
第五章以钟声闻于外,兴申后被废之事必然国人皆知。俗语“没有不透风的墙”,此之谓也。自己已经被废,心却念念不忘,于是有了“念子懆懆”的弃妇;既已弃之,必先厌之,于是有了“视我迈迈”的无情丈夫。对比中弃妇的善良和顺、丈夫的轻薄无情显得更为鲜明。
第六章诗意与第四章相近,以鹤鹙失所兴后妾易位。同时鹤的洁白柔顺和鹙的贪婪险恶与申后和褒姒之间存在着隐喻关系。“妖大之人”的媚惑实在是女主人公被弃的一个重要原因,难怪她一次次地“维彼硕人,实劳我心”,想起那个妖冶之人就不能不心情沉痛了。
第七章以总是偶居不离的鸳鸯相亲相爱,适得其所,反兴无情无德的丈夫不能与自己白头偕老的悖德举动。这一章要与第四、五、六章连起来读才会更深一层地理解弃妇的怨恨。她实际上是在说:虽然那个妖冶的女人很有诱惑力,如果做丈夫的考虑天理人情而不是“二三其德”,就不会有今天的结果。
诗最后一章以扁石被踩的低下地位兴申后被黜之后的悲苦命运。被遗弃的妇人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命运,“之子之远,俾我疧兮”。面对茫然不知的前途,必然忧思成疾。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诗的首章以咏叹始,三句以“兮”煞尾,末章以咏叹终,亦以“兮”字结句。中间各章语气急促,大有将心中苦痛一口气宣泄干净的气势。缓急之间,颇有章法,诵读之时有余音绕梁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