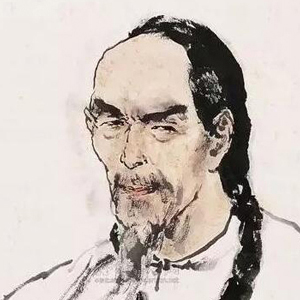《招隐士》给人一种森然可怖,魂悸魄动的特殊感受。作者以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采用夸张、渲染的手法,极写深山荒谷的幽险和虎啸猿悲的凄厉,造成怵目惊心的艺术境界,成功地表达了渴望隐者早日归还的急切心情。通篇感情浓郁,意味深永,音节谐和,情辞悱恻动人,为后代所传诵。通过对山水、溪谷、巉岩以及奔突吼叫在深林幽谷间的虎豹熊罴的描绘,以将山水景物经过浓缩、夸张、变形处理,使自然界的飞禽走兽和真山真水变成艺术形象的方法,渲染出一种幽深、怪异、可饰的环境气氛,弥漫着郁结、悲怆、而又缠绵悱恻的情思,表现了王孙不可久留的主题思想。让人们仿佛听到一声声回荡在崖谷间“王孙兮归来!”那招魂般凄厉哀怨的呼唤。
山中景物之惊心可怖暗示朝中政治形势的复杂和淮南王处境的危险,并以淮南王喜爱的楚辞形式予以规劝,这样的揣测应该是比较合乎情理的。
全文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从篇首至“蟪蛄鸣兮啾啾”。主要描写为追慕桂枝芬芳(象征美德)的王孙在虎豹出没、猿猨哀鸣的深山幽壑间淹留,引起亲朋好友的焦虑与不安,并以春草、秋螀写作者萦回之思和怊怅之情。
第二部分从“坱兮轧”始至篇末,以山石之巍峨,雾岚之郁结,虎豹之奔突,林木之幽深,极力渲染山中之阴森可怕,并以离群禽兽失其类的奔走呼叫,规劝王孙之归来。
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步《楚辞》之余芳,另劈别径,“衔其山川”、“猎其艳词”表达出深曲的情致和婉转怊怅的意绪。所谓“衔其山川”,指此篇对山川景物、烟岚林莽的环境描写,及其描写中运用比兴象征、气氛烘托等艺术手法,主要是从屈宋辞赋中移植、借鉴过来然后重加剪辑而别出机杼的。在对山川景物、烟岚林莽或虎豹走兽的描写,尤其将自然界经过一番浓缩、夸张、变形处理,渲染气氛,使之成为人神杂糅的艺术形象和艺术境界上,屈宋辞赋中早已有许多成功的范例,这可以以《九歌·山鬼》,《九章·涉江》为代表。
《山鬼》对山中之神所处幽深昧险的环境描写是:“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云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昼晦”、“采三秀兮于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描写以雷声、雨声、风声、木声、猨狖鸣声,组成萧瑟而令人怵目惊心的山中夜半:“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
《涉江》对屈原独处深山幽昧环境的描写同样慑人心魄:“入溆浦余佪兮,迷不知吾之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另外,与山川景物、林深猨鸣的描绘相对应,《山鬼》中写了“独处”“山之阿”的山中女神;《涉江》中出现了“独处乎山中”的屈原自我形象。而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正是以屈原作品中山川景物、环境气氛的渲染烘托和山中人感情效应的描写为张本而发端,进一步高浓度地描写山中崖断路绝、虎豹纵横的险恶景象,然后将“攀援桂枝”的王孙置之其间的。王孙是古代对贵族子弟和一般男子的尊称。《史记·淮阴侯列传》:“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司马贞《索引》:“言王孙公子,尊之也。”这里指所招和思念的人。也有学者以为:“淮南王刘安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王曰:吾高帝孙,亲行仁义……’称刘安为王孙,身份极为适当”(见马茂元《楚辞选》)。
在描写山川景物、环境气氛时,《招隐士》写了山石之突兀,草木之荒芜,禽兽之奔突,虫声之哀鸣。写山石的有“石嵯峨”、“溪谷崭岩”、“坱兮轧、山曲岪”、“嵚岑碕礒兮,碅磳磈硊”。其中“嵯峨”、“崭岩”、“坱”、“轧”、“曲岪”、“嵚岑碕礒”、“碅磳磈硊”都是形容山高路险、崎岖曲折和荦确不平之貌。写草木的有“偃蹇连蜷兮枝相缭”、“春草生兮萋萋”、“丛薄深林兮人上栗”、“树轮相纠兮,林木茷骫。青莎杂树兮,薠草靃靡”。写禽兽奔突、虫声哀鸣的有“猿狖群啸兮虎豹嗥”、“虎豹穴”、“白鹿麏麚兮,或腾或倚”、“猕猴兮熊罴,慕类兮以悲”,“虎豹斗兮熊罴咆”、“蟪蛄鸣兮啾啾”等。
首二句“桂树丛生兮山之幽,偃蹇连蜷兮枝相缭”,以描写南方珍贵名木桂树蟠曲交柯之姿和色泽芬芳象征的君子懿德为起,而与下王孙“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相呼应,写法与《山鬼》首二句“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类似,均首句出现贞洁芬芳的抒情形象,次句进一步修饰。其中树生“山之幽”,与人在“山之阿”句式亦相同。王孙滞留山中的原因是“攀援桂树”(追慕圣贤之德),与《涉江》中屈原“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的表白相近。不同的是,《招隐士》改变了《山鬼》中的抒情气氛和《涉江》环境描写中的愁苦色彩,亟写山中景象之险恶。《山鬼》的环境描写,是为了表现山中女神“怨公子兮怅忘归”的情愫,《涉江》的环境描写,是为了抒发屈原“济乎江湘”的悲戚;而《招隐士》中的王孙,仅仅是一个被召唤的对象,并没有《山鬼》和《涉江》中主人公的哀怨抒发和内心独白。这种描写,只在篇末对王孙归来的呼唤声中才化成一种感情因素,成为一种缠绵、悲凉的情绪充塞读者心间而驱之不去。
在“猎其艳词”方面,《招隐士》中叠字的运用亦引人注目。《楚辞》中多用叠字,《山鬼》中即以“云容容”、“杳冥冥”、“石磊磊”、“葛蔓蔓”、“雷填填”、“雨冥冥”、“猨啾啾”、“风飒飒”、“木萧萧”,渲染烘托出失恋女神愁思百结、孤独无依的寂寞情怀和悲秋意绪。顾炎武《日知录》说:“诗用叠字最难”,“宋玉《九辩》‘乘精气之抟抟兮,骛诸神之湛湛。骖白霓之习习兮,历群灵之丰丰。左朱雀之苃苃兮,右苍龙之跃跃。属雷师之阗阗兮,通飞廉之衙衙。前轻轲之锵锵兮,后辎车之从从。载云旗之委蛇兮,扈屯骑之容容’。连用十一叠字,后人辞赋,亦罕及之者。”淮南小山即吸取了屈、宋诗篇中善用叠字的修辞手法,在《招隐士》中用了“啾啾”、“萋萋”、“峨峨”、“凄凄”、“漎漎”等叠字,并以“春草萋萋”、“蟪蛄鸣啾啾”暗示时间变化,表明对王孙一去不归的哀叹;其中运用屈宋诗篇中回环复沓的节奏,铿锵而又有时急促音调上的处理。对“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的复迭,以及“虎豹嗥”、“虎豹穴”、“虎豹斗”复迭整齐中的变化;诗中三字、四字、五字、六字、七字、八字句式奇妙地交错运用,遂使《招隐士》“音节局度,浏亮昂激”。
除此而外,《招隐士》所以有别于东方朔、王褒、刘向、扬雄等人的拟骚之作而独秀其类,嗣音屈宋,取得惊心动魄的艺术魅力,还因为它在思想主题、篇章结构表现上的单纯、提炼和集中。在主题上,《招隐士》删去了一切可能会冲淡主题的枝蔓。诗中既没有明确地写招唤者为什么要劝王孙归来,也没有说明王孙与招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更没有让王孙去作志行高洁的自我披露和内心独白——作者根本没有让王孙开口说话,王孙在诗中,如前所述,只是一个被召唤者日夜思念的攀援桂枝的高洁形象。全诗的思想主题仅是一句咏叹调般单纯、明朗、集中的呼唤——“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久留!”千年以来,一直回荡在人们的心里。
作者通过谴责人们对梅花的摧残,形象地揭露和抨击了清王朝统治阶级束缚人民思想,压制、摧残人才,表达了要求改革政治、追求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
本文篇幅短小,结构严谨,寓意深刻。全文一共三段。
第一段,揭示产生病梅的根源。文章起笔先简要叙述梅的产地:“江宁之龙蟠,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皆产梅。”然后笔锋一转,引出一段有些人评价梅的美丑,用“固也”一语轻轻收住。接着,作者开始详细分析病梅产生的缘由。原来,在“文人画士”的心目中,梅虽然“以曲为美”“以欹为美”“以疏为美”。但一“未可明诏大号”;二不能让人“以夭梅、病梅为业以求钱”;三,从客观上说又不能“以其智力为也”。所以,他们只好通过第四个途径了。于是,他们暗通关节,让第三者来转告“鬻梅者”,斫正,删密,锄直,以投“文人画士孤癖之隐”。在这样的情况下,“江南之梅皆病”也就无可避免了。“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一句感叹,道出了作者的无尽愤慨,也为下文“誓疗之”蓄足了情势。
第二段,写作者疗梅的行动和决心。“予购三百盆”而“誓疗之”,可见其行动的果断;“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可见其成功的誓言;“甘受诟厉,辟病梅之馆”,可见其坚持到底的决心。疗梅的举动和决心,写尽了作者对封建统治阶级压制人才、束缚思想的不满和愤慨,表达了对解放思想、个性自由的强烈渴望。
第三段,写作者辟馆疗梅的苦心。这一段,作者慨叹自己暇日不多,闲田不多,疗梅的力量有限,也就是慨叹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挽回人才受扼杀的黑暗的政局。事实上,作者一生在仕途上很不得意,只做过小京官,而且受到权贵的歧视和排挤,自己的才能都无法施展,更不要说解除全国人才所遭受的扼制了。因此,他只能以感叹作结。但是,虽为感叹,他渴望“广贮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充分表现了他坚持战斗的意志。
本文表面上句句说梅,实际上却是以梅喻人,字字句句抨击时政,寓意十分深刻。作者借文人画士不爱自然健康的梅,而以病梅为美,以至使梅花受到摧残,影射统治阶级禁锢思想、摧残人才的丑恶行径。“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暗示的正是那些封建统治者的帮凶,他们根据主子的意图,奔走效劳,以压制人才为业。斫正、删密、锄直,这夭梅、病梅的手段,也正是封建统治阶级扼杀人才的恶劣手段;他们攻击、陷害那些正直不阿、有才能、有骨气、具有蓬勃生气的人才,要造就的只是“旁条”和生机窒息的枯干残枝,亦即屈曲、邪佞和死气沉沉的奴才、庸才。作者“购三百盆”,“泣之三日”,为病梅而泣,正是为人才被扼杀而痛哭,无限悲愤之中显示了对被扼杀的人才的深厚同情。“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就是说要破除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才的束缚、扼制,让人们的才能获得自由发展。“必复之全之”,一定要恢复梅的本性,保全梅的自然、健康的形态。这正反映了作者要求个性解放,“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迫切心情。由此可见,本文表面写梅,实际是借梅议政,通过写梅来曲折地抨击社会的黑暗,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
这是一篇典型的战争诗。诗人以袒露自身与主流意识的背离,宣泄自己对战争的抵触情绪。作品在对人类战争本相的透视中,呼唤的是对个体生命具体存在的尊重和生活细节幸福的获得。这种来自心灵深处真实而朴素的歌唱,是对人之存在的最具人文关 怀的阐释,是先民们为后世的文学作品树立起的一座人性高标。
《毛诗序》云:“《击鼓》,怨州吁也。”郑笺以《左传·隐公四年》州吁伐郑之事实之。姚际恒《诗经通论》以为“与经不合者六”,此实乃《春秋·宣公十二年》“宋师伐陈,卫人救陈”之事,在卫穆公时。今以为姚说较《毛序》为合理,姑从姚氏。
第一章总言卫人救陈,平陈宋之难,叙卫人之怨。结云“我独南行”者,诗本以抒写个人愤懑为主,这是全诗的线索。诗的第三句言“土国城漕”者,《鄘风·定之方中》毛诗序云:“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居漕邑,齐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文公营楚丘,这就是诗所谓“土国”,到了穆公,又为漕邑筑城,故诗又曰“城漕”。“土国城漕”虽然也是劳役,犹在国境以内,南行救陈,其艰苦就更甚了。
第二章“从孙子仲,平陈与宋”,承“我独南行”为说。假使南行不久即返,犹之可也。诗之末两句云“不我以归,忧心有忡”,叙事更向前推进,如芭蕉剥心,使人酸鼻。
第三章写安家失马,似乎是题外插曲,其实文心最细。《庄子》说:“犹系马而驰也。”好马是不受羁束、爱驰骋的;征人是不愿久役、想归家的。这个细节,真写得映带人情。毛传解释一二句为:“有不还者,有亡其马者。”把“爰”解释为“或”,作为代词,则两句通叙营中他人。其实全诗皆抒诗人一己之情,所以四、五两章文情哀苦,更为动人。
第四章“死生契阔”,毛传以“契阔”为“勤苦”是错误的。黄生《义府》以为“契,合也;阔,离也;与死生对言”是正确的。至于如何解释全章诗义。四句为了把叶韵变成从AABB式,次序有颠倒,前人却未尝言及。今按此章的原意,次序应该是:
执子之手,与子成说;死生契阔,与子偕老。
这样诗的韵脚,就成为ABBA式了。本来“死生契阔,与子偕老”,是“成说”的内容,是分手时的信誓。诗为了以“阔”与“说”叶韵,“手”与“老”叶韵,韵脚更为紧凑,诗情更为激烈,所以作者把语句改为这一次序。
第五章“于嗟阔兮”的“阔”,就是上章“契阔”的“阔”。“不我活兮”的“活”,应该是上章“契阔”的“契”。所以“活”是“佸”的假借,“佸,会也。”“于嗟洵兮”的“洵”,应该是“远”的假借,所以指的是“契阔”的“阔”。“不我信兮”的“信”,应该是“信誓旦旦”的“信誓”,承上章“成说”而言的。两章互相紧扣,一丝不漏。
“怨”是《击鼓》一诗的总体格调与思想倾向。从正面言,诗人怨战争的降临,怨征役无归期,怨战争中与己息息相关的点滴幸福的缺失,甚至整个生命的丢失。从反面言,诗作在个体心理,行为与集 体要求的不断背离中,在个体生命存在与国家战事的不断抗衡中,在小我的真实幸福对战争的残酷的不断颠覆中,流显出一份从心底而来的厌战情绪。这一腔激烈的厌战之言,要争取的是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尊重,是生活细节中的切实幸福。
这首诗是送别之作,写的是送同僚入京买马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题材。
诗的前两句照应题目,“入京”二字写京城长安一带景色。“晚”和“夕阳”点出送别时间,而“关树”、“长安”为何远所去之处,暗示“入京”,同时勾划出苍茫远景。诗的三、四两句写近景。阵阵回风,蒙蒙细雨,伴着送别酒席,打湿旅人行装,从而把环境与送别自然联系起来,意境颇为别致,而“送”字自在其中。
诗的五、六两句转写此行意义。“边尘黑”点明战争未息,“塞草黄”点明时已深秋。经这里点明“秋”字,上文的“关树”、“回风”、“细雨”等等景物便都觉得真切。这两句言及边地战争,可见诗人身在虢州,心系边塞。诗的结尾两句承“习战”、“防秋”,点明“市马”。“市马”本为“习战”,诗人却由此想到“燕昭市骏”的色而且用“不是学燕王”来说何远此行性质,似乎包含弃置州县,不被看重的叹息。
诗的首联写“关树晚苍苍,长安近夕阳”,是惜“入京”而写自己“唯有乡园处,依依望不迷”(《早秋与诸子登虢州西亭观眺》)的情态;诗的尾联出“市骏马”而联想到“学燕王”,也包含着“丹心亦未休”(《题虢州西楼》)却又无人赏拔的含义。这正是本诗表现上的一个特点。此外,诗中还表达了对边事的关切。这些都可以反映诗人任职虢州期间思想和生活的一个侧面。
这是一首祝酒歌。前两句敬酒,后两句祝辞。话不多,却有味。诗人以稳重得体的态度,抒写豪而不放的情意,在祝颂慰勉之中,道尽仕宦浮沉的甘苦。
古人用“金屈卮”敬酒,以示尊重。诗人酌满金屈卮,热诚地邀请朋友干杯。“不须辞”三字有情态,既显出诗人的豪爽放达,又透露友人心情不佳,似乎难以痛饮,于是诗人殷勤地劝酒,并引出后两句祝辞。
从后两句看,这个宴会大约是饯饮,送别的那个朋友大概遭遇挫折,仕途不利。对此诗人先作譬喻,大意说,你看那花儿开放,何等荣耀,但是它还要经受许多次风雨的摧折。言外之意是说,大自然为万物安排的生长道路就是这样曲折多磨。接着就发挥人生感慨,说人生其实也如此,就要尝够种种离别的滋味,经受挫折磨炼。显然,诗人是以过来人的体验,慰勉他的朋友。告以实情,晓以常理,祝愿他正视现实,振作精神,可谓语重心长。
于武陵一生仕途不达,沉沦不僚,游踪遍及天南地北,堪称深谙“人生足别离”的况味的。这首《劝酒》虽是慰勉朋友之作,实则也是自慰自勉。正因为他是冷眼看人生,热情向朋友,辛酸人作豪放语,所以形成这诗的独特情调和风格,豪而不放,稳重得体。后两句具有高度概括的哲理意味,近于格言谚语,遂为名句,颇得传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