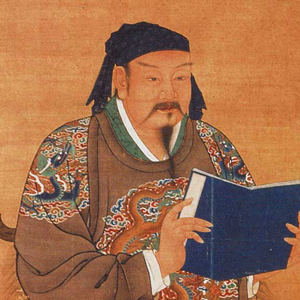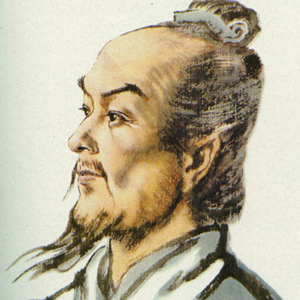这是韩偓晚年寓居南安之作,与《安贫》表现同一索寞情怀,而写法上大不相同。《安贫》直抒胸臆,感慨万端;此篇则融情入景,兴寄深微。
春尽,顾名思义是抒写春天消逝的感慨。韩偓的一生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变故,晚年寄身异乡,亲朋息迹。家国沦亡之痛,年华迟暮之悲,孤身独处之苦,有志难骋之愤,不时袭上心头,又面临着大好春光的逝去,内心的抑郁烦闷自不待言。郁闷无从排遣,唯有借酒浇愁而已。诗篇一上来,就抓住醉酒这个行为来突出“惜春”之情。不光是醉,而且是连日沉醉,醉得昏昏然,甚且醉后还要继续喝酒,以致衣服上溅满了斑斑酒痕。这样反复渲染一个“醉”字,就把作者悼惜春光的哀痛心情揭示出来了。
颔联转入写景。涓细的水流载着落花漂浮而去,片断的云彩随风吹洒下一阵雨点。这正是南方暮春时节具有典型特征的景象,作者把它细致地描画出来,逼真地传达了那种春天正在逝去的气氛。不仅如此,在这一幅景物画面中,诗人还自然地融入了自己的身世之感。那漂浮于水面的落花,那随风带雨的片云,漂泊无定,无所归依,正是诗人自身沦落无告的象征。扩大开来看,流水落花,天上人间,一片大好春光就此断送,也可以看作诗人深心眷念的唐王朝终于被埋葬的表征。诗句中接连使用“细”、“浮”、“别”、“断”、“孤”这类字眼,更增添了景物的凄清色彩,烘托了诗人的悲凉情绪。这种把物境、心境与身境三者结合起来抒写,达到融和一体、情味隽永的效果,正是韩偓诗歌写景抒情的显著特色。
颈联再由写景转入抒情。为什么要说“人闲易有芳时恨”,大凡人在忙碌的时候,是不很注意时令变化的;愈是闲空,就愈容易敏感到季节的转换,鸟啼花落,处处都能触动愁怀。所以这里着力点出一个“闲”字,在刻画心理上是很精微的。再深一层看,这个“闲”字上还寄托了作者极深的感慨。春光消去,固然可恨,尤可痛心的是春光竟然在人的闲散之中白白流过,令人眼瞪瞪望着它逝去而无力挽回。这正是诗人自己面临家国之变而不能有所作为的沉痛告白。下联“地迥难招自古魂”,则把自己的愁思再转进一层。诗人为惜春而寄恨无穷,因想到:如有亲交故旧,往来相过,互诉心曲,也可稍得慰藉,怎奈孤身僻处闽南,不但见不到熟悉的今人,连古人的精灵也招请不来,更叫人寂寞难堪。当然,这种寂寥之感虽托之于“地迥”,根本上还在于缺乏知音。“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韩偓此时的孤愤心情,同当年的陈子昂确有某种相通之处。
七、八句抛开议论事理,转入抒情。借流莺相顾、春愁略解,含蓄地表达了对“春尽”的感伤和悲叹之情。诗人在这里虽然没有具体写自己是如何苦闷,表面上冲淡了全诗的悲剧色调,但其无限苦闷之情却形象地表现出来。
这首诗有叙述,有描写,有议论,三者紧密结合是其主要特点。这首诗描写景物具体形象,“细水浮花归别洞,断云含雨入孤村”这些诗句,真实地描绘出春天雨前农村的美景,有很大的艺术魅力。这首诗语言流畅优美,对仗工整。通篇扣住“春尽”抒述情怀,由惜春引出身世之感、家国之悲,一层深一层地加以抒发,而又自始至终不离开春尽时的环境景物,即景即情,浑然无迹,这就是诗篇沉挚动人的力量所在。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惜别伤春连日来酒醉昏昏,醒来之后衣裳上全是酒痕。
细水上漂着落花流入另涧,阴见带雨飘入那远处孤村。
闲居无聊恨芳时白白流去,异地千里难招来古人精魂。
最感激流莺掀转深情厚意,每当清晨还特意飞到西园。
注释
惜春:爱怜春色。
酒痕:酒污的痕迹。
浮:一作“漾”。
别涧:另外一条河流。涧,一作“浦”。
断云:片片云朵。
人闲:作者在朱全忠当权时,被贬到濮州,后来依附他人,终日无所事事。
有:一作“得”。
芳时恨:就是春归引起的怅恨。终日闲呆,不能有所作为,辜负了大好时光,故有“芳时恨”之感。芳时,指春天。
地迥:地居偏远。迥:一作“胜”。
古魂:故人的精魂,指老友已故化为精魂。
流莺:叫声悦耳的莺。流,谓其鸣声婉转悦耳。
厚意:深情厚意。
这是韩偓晚年寓居南安之作,与《安贫》表现同一索寞情怀,而写法上大不相同。《安贫》直抒胸臆,感慨万端;此篇则融情入景,兴寄深微。
春尽,顾名思义是抒写春天消逝的感慨。韩偓的一生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变故,晚年寄身异乡,亲朋息迹。家国沦亡之痛,年华迟暮之悲,孤身独处之苦,有志难骋之愤,不时袭上心头,又面临着大好春光的逝去,内心的抑郁烦闷自不待言。郁闷无从排遣,唯有借酒浇愁而已。诗篇一上来,就抓住醉酒这个行为来突出“惜春”之情。不光是醉,而且是连日沉醉,醉得昏昏然,甚且醉后还要继续喝酒,以致衣服上溅满了斑斑酒痕。这样反复渲染一个“醉”字,就把作者悼惜春光的哀痛心情揭示出来了。
颔联转入写景。涓细的水流载着落花漂浮而去,片断的云彩随风吹洒下一阵雨点。这正是南方暮春时节具有典型特征的景象,作者把它细致地描画出来,逼真地传达了那种春天正在逝去的气氛。不仅如此,在这一幅景物画面中,诗人还自然地融入了自己的身世之感。那漂浮于水面的落花,那随风带雨的片云,漂泊无定,无所归依,正是诗人自身沦落无告的象征。扩大开来看,流水落花,天上人间,一片大好春光就此断送,也可以看作诗人深心眷念的唐王朝终于被埋葬的表征。诗句中接连使用“细”、“浮”、“别”、“断”、“孤”这类字眼,更增添了景物的凄清色彩,烘托了诗人的悲凉情绪。这种把物境、心境与身境三者结合起来抒写,达到融和一体、情味隽永的效果,正是韩偓诗歌写景抒情的显著特色。
颈联再由写景转入抒情。为什么要说“人闲易有芳时恨”,大凡人在忙碌的时候,是不很注意时令变化的;愈是闲空,就愈容易敏感到季节的转换,鸟啼花落,处处都能触动愁怀。所以这里着力点出一个“闲”字,在刻画心理上是很精微的。再深一层看,这个“闲”字上还寄托了作者极深的感慨。春光消去,固然可恨,尤可痛心的是春光竟然在人的闲散之中白白流过,令人眼瞪瞪望着它逝去而无力挽回。这正是诗人自己面临家国之变而不能有所作为的沉痛告白。下联“地迥难招自古魂”,则把自己的愁思再转进一层。诗人为惜春而寄恨无穷,因想到:如有亲交故旧,往来相过,互诉心曲,也可稍得慰藉,怎奈孤身僻处闽南,不但见不到熟悉的今人,连古人的精灵也招请不来,更叫人寂寞难堪。当然,这种寂寥之感虽托之于“地迥”,根本上还在于缺乏知音。“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韩偓此时的孤愤心情,同当年的陈子昂确有某种相通之处。
七、八句抛开议论事理,转入抒情。借流莺相顾、春愁略解,含蓄地表达了对“春尽”的感伤和悲叹之情。诗人在这里虽然没有具体写自己是如何苦闷,表面上冲淡了全诗的悲剧色调,但其无限苦闷之情却形象地表现出来。
这首诗有叙述,有描写,有议论,三者紧密结合是其主要特点。这首诗描写景物具体形象,“细水浮花归别洞,断云含雨入孤村”这些诗句,真实地描绘出春天雨前农村的美景,有很大的艺术魅力。这首诗语言流畅优美,对仗工整。通篇扣住“春尽”抒述情怀,由惜春引出身世之感、家国之悲,一层深一层地加以抒发,而又自始至终不离开春尽时的环境景物,即景即情,浑然无迹,这就是诗篇沉挚动人的力量所在。
韩偓(844年-923年),字致光,号致尧,小字冬郎,号玉山樵人,京兆万年(今陕西省西安市)人。晚唐大臣、诗人,翰林学士韩仪之弟,“南安四贤”之一。唐昭宗龙纪元年(889年),进士及第,出佐河中节度使幕府。入为左拾遗,转谏议大夫,迁度支副使。光化三年(900年),从平左军中尉刘季述政变,迎接唐昭宗复位,授中书舍人,深得器重。黄巢进入长安,随驾进入凤翔,授兵部侍郎、翰林承旨,拒绝草诏起复前任宰相韦贻范。不肯依附于梁王朱全忠,贬为邓州司马。唐昭宗遇弑后,依附于威武军节度使王审知,寓居九日山延福寺。信仰道教,擅写宫词,多写艳情,词藻华丽,人称“香奁体”。后梁龙德三年(923年),病逝于南安县龙兴寺,安葬于葵山。著有《玉山樵人集》。 ▶ 307篇诗文
这首词是在写在凌晨天还没亮时爬上山顶凭高远望的感受,这首词的境界中都含有对人生之了悟的成分。
王国维特别善于写景,“高峡流云彩,人随飞鸟穿云去”写出了一种类似杜甫“荡胸生曾云彩,决眦入归鸟”的那种攀登到半山高处所特有的景象。山下刚刚下过雨,山顶是晴天,山腰处乱云飞动,正是雨收而云未散的时候。“数峰着雨,相对青无语”,似乎是套用了姜夔《点绛唇》的“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这里“相对”解释为人与“数峰”的相对要好些。因为对面青山一直就在那里静静地看着人在云雾里攀登,而人却是在穿过半山的云雾之后才注意到这“着雨”的青山。青山虽然不会说话,却在以雨后的美丽令人惊喜。
“岭上金光,岭下苍烟沍”是说:抬头看,朝阳初照的峰顶已然在望;低头看,脚下深谷苍烟凝结,一片昏暗。因为在这里,从“岭下苍烟沍”到“人间曙,疏林平楚,历历来时路”这有一个时间的过程:随着太阳的渐渐升高,黑暗山谷中的景色也渐渐能够看清了,刚才攀登途中所经过的那些高高低低的丛林,如今都已落在自己脚下。“历历”,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样子,同时也是对往事和过去的回忆,用在这里具有一定的哲理的味道。在山下仰望攀登的道路,只能有“危乎高哉”的惊叹而说不上“历历”;只有在经过艰苦的攀登穿越乌云彩见到光明时才能够有这种“历历”的回顾和反省。
这是一首记游诗,诗作于池州,一反其词的激昂悲壮,以清新明快的笔法,抒写了他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真挚热爱,体现了马背赋诗的特点。
前两句写出游的愉悦。起句“经年尘土满征衣”写长期紧张的军旅生活。诗人从军后,一直过着紧张的军事生活,特别是在抗金斗争中,为了保卫南宋残存的半壁河山,进而恢复中原,他披甲执锐,率领军队,冲锋陷阵,转战南北,长期奔波,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保卫国家的伟大事业之中。诗的开头一句正是对这种紧张军旅生活的生动朴实的高度概括。“经年”,这里指很长时间以来。“征衣”,这里是指长期在外作战所穿的衣服。既然长年累月地率领部队转战南北,生活十分紧张,那就根本没有时间、没有心思去悠闲地游览和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愈是这样,愈盼望有朝一日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这样,起笔一句就为下面内容的引出作了充分的渲染和铺垫,看似与记游无关,而作用却在于突出、强调和反衬了这次出游的难得与可贵。
故对句以“特特寻芳上翠微”接住。现在,诗人竟然有了这样的机会,到齐山观览,而且登上了著名诗人杜牧在这里建造的翠微亭,心里一定愉快、兴奋。“特特”,在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当特别、特地讲,起了强调、突出的作用,以承接首句意脉,一是指马蹄声,交待了这次出游是骑马去的,成为诗歌结尾一句的伏笔。“寻芳”,探赏美好的景色。“翠微”,是诗人到达的地方。这样,对句实际上写了出游的方式(骑马)和到达的地点(翠微亭),从而起到了点题、破题的作用。诗的开头两句,首句起笔突兀,如高山坠石,不知其来,似与题目无关,而实为次句铺垫;次句陡转笔锋扣题,承接自然,成为首句的照应;两句相互配合,表现出作者大起大落、大开大阖的高度艺术腕力和高屋建瓴的雄伟气魄。两句形成了波澜和对比,从而突出了这次出游的欣喜。
“好水好山看不足,马蹄催趁月明归。”诗的三四两句并没有象一般的记游诗那样,对看到的景色作具体细致的描述,而是着眼于主观感觉,用“好水好山”概括地写出了这次“寻芳”的感受,将秀丽的山水和优美的景色用最普通、最朴实、最通俗的“好”字来表达,既有主观的感受,又有高度的赞美。同时,又用“看不足”传达自己对“好水好山”的喜爱、依恋和欣赏。
结尾一句则写了诗人为祖国壮丽的山河所陶醉,乐而忘返,直到夜幕降临,才在月光下骑马返回。“马蹄”,照应了上面的“特特”。“催”字则写出了马蹄声响使诗人从陶醉中清醒过来的情态,确切而传神。“月明归”,说明回返时间之晚,它同上句的“看不足”一起,充分写出了诗人对山水景色的无限热爱、无限留恋。岳飞之所以成为民族英雄,之所以为自己的国家英勇战斗,同他如此热恋祖国的大好河山是密不可分的。诗的结尾两句正表现了作者对祖国山河特有的深厚感情。
这首诗通过记游,抒发了作者对祖国山河无限深厚的热爱之情。在艺术上运思巧妙,不落俗套,虽是记游,而不具体描述景物,重在抒写个人感受。其结构方式除以时间为序外,又把情感的变化作为全诗的线索,突出了这次出游登临的喜悦。语言通俗自然,明白如话。
全文分为三大部分。从开头到“归母氏而后宁”为第一部分,叙说远游之因。先说主观高洁志行:仰慕先哲仁义贞节,遵循法度,抱负远大,并不断加强道德修养。再说客观悲惨遭遇:“奋余荣而莫见兮,播余香而莫闻。”徒有忠君报国之志却无人理解;“行陂僻而获志兮,循法度而离殃。”君主不分贤愚善恶;“冀一年之三秀兮,遒白露之为霜。”不断遭到小人的谗害。内心的美好理想与现实的残酷打击造成强烈的情感反差,使作者痛苦不堪。而他又生性耿介,不肯顺应时俗,偏偏“愿竭力以守义兮,虽贫穷而不改”,“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尝。”故落得“何孤行之茕茕兮,孑不群而介立”的孤独特立的处境和生不逢时的感伤,故燃起远游自娱、求索理想的欲望,“想依韩以流亡”。故就岐山向善于卜筮的古代贤君周文王陈述情怀,请求指点。文王占得的卦意是:“远走高飞保全名声为大吉大利。历览众山四处周游,振翼凭急风高扬美名。二女动情于高山,寒冰毁折不可经营。天高尚可变为水泽,谁云道路不平不可行。你占得的是栖鹤兆,鹤子只有回到母鹤处才会得安宁。”文王所占既引发了下面远游六合的情节,又预见了情节的发展与结局;既告诉说远游道路坎坷,又鼓励说要尽力远游去寻求贤君。文王的占卜坚定了作者远逝自疏、躲避谗言、另求贤君、实现理想的信念。
从“占既吉而无悔兮”到“临旧乡之暗蔼”为第二大部分,写远游的经过。一游东方。登上蓬莱仙山,顿有远离世俗之累飘然欲仙的欣喜,但这里只能是“留瀛洲而采芝兮,聊且以乎长生”,而这并不是远游的目的。这时作者突然忆起曾梦见生长在昆仑山上的木禾,就产生亲登昆仑山的念头,于是指向西南奔向昆仑。
二游南方。凭吊了大禹、重华、祝融的旧地,登上日行正中的昆吾,并在昼夜喷吐烈焰的火山边休息,酷热难耐,倍感孤独,于是再向西行。
三游西方。经行都广的建木神树之下,拾取神树若木的花朵。虽此地之人寿命都在千岁之上,但这也不是他所追求的,故又继续前行。
四游九州中原。在黄河之滨请黄帝为他占卜前程。黄帝历数神话传说、历史典故以为据,告诉他“死生错而不齐兮,虽司命其不晰。”反复论说祸福相因,难以预测,贤愚杂糅,难以分辨,但要相信一条“彼天监之孔明兮,用棐枕而佑仁。”苍天所视明察秋毫,它会辅助诚实仁德之人。善行必有善报,但要尽力求索,不能坐等机遇,最后嘱告说:“盍远迹以飞声兮,孰谓时之可蓄?”故作者重振远游之志,继续求索前行。
五游北方。作者极度渲染北方的寒冷:“行积冰之硙硙兮,清泉冱而不流。寒风凄而永至兮,拂穹岫之骚骚。”以至使北方神兽玄武与螣蛇都冻得或缩入壳中,或盘缩一团。在这阴极之地,又念起阴中之阴,故纵身下潜。
六游地下。没想到地下远不如海外四方,故作者只是“趋谽谽谺之洞穴兮,标通渊之碄碄。经重阴乎寂寞兮,愍坟羊之潜深。”匆匆而过,就“追慌忽于地底兮,轶无形而上浮。”再度升天,飞向西北。
七游西北钟山。在这里凭吊了祖江神,会见了西王母,又遇到了太华玉女、洛浦宓妃二位女神。二位女神体态妖娆,光彩照人,并赠玉佩缯绮以通情谊,但这些外在的形貌重物并不是作者所追求的,作者汲汲以求的是内在情志的契合,故曰:“虽色艳而赂美兮,志浩荡而不嘉。”不及答赋,匆匆前行。此即应合了文王所占:“二女感于崇岳兮,或冰折而不营。”
八游昆仑。终于来到梦中所念之地,作者纵情驰游,并再次请巫咸为他占卜曾见木禾的梦。巫咸占曰:“既垂颖而顾本兮,尔要思乎故君。安和静而随时兮,姑纯懿之所庐。”巫咸所占预示了远游的结局,故作者虽受到百神的热烈欢迎;虽内心非常羡慕光辉灿烂的天上仙都;虽终于寻到远祸全身的乐土;虽能唯意所适,纵情畅游,但远祸全身的欢悦并没有淹没忠君恋土的哀愁,所以当他“据开阳而頫盼兮,临旧乡之暗蔼”之时,内心斗争更为激烈,最后只有放弃了一己的欢悦,而以生命为代价去恪守忠君爱国的贞节。即便在冥冥幻想之中他也不忍离开君国于一步。
从“悲离居之劳心兮”至结尾为第三部分,写远游的结局。作者从天上回落人间,从光明的幻想中回到黑暗的现实中,欲进不能,欲离不忍,无可奈何之中只好洁身自好,独善其身,退修初服,归耕田园,“心远地自偏”,思玄聊自慰。并卒章显其志,以诗总括全文主旨。
这篇赋最突出的艺术特色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从其表现内容、情感上看:作者借梦幻远游的浪漫主义形式抒发现实生活中的哀愁。他主观抒发的虽是一已的悲哀,但客观上不仅塑造了志行高洁的自我形象,而且也揭示了汉代政治舞台上的斗争与黑暗,揭露了阉党谗害贤良的丑恶,揭露了君主不分善恶的昏庸。悲哀之中有不满,有反抗,压抑之中有高扬,而对美好境界的追求更带有理想化的浪漫主义色彩。从其表现方法看:既有如实的直述,更有虚构的幻想。作者融汇神话传说、历史典故乃至阴阳五行、龟卜草筮、天文地理、虫鱼草木编织远游上下四方的情节,通过叙说幻想虚构的情节抒发对现实的不满,对理想的追求。并将海外众仙、历史人物、天上星宿、卜筮卦象、花草鸟兽、服装玉饰构成六大意象群,其中又多分为性质相对的两组分别象征着光明与丑恶,它们已不是孤立的比喻,而是群体的象征。作者不仅赋神仙、历史人物以生命,甚至还赋卦象、星宿以生命,共同参与他上天入地的求索,如文王所占:“二女感于崇岳兮,或冰折而不营。”“遇九皋之介鸟兮,怨素意之不逞。游尘外之瞥天兮,据冥翳而哀鸣。”“二女”、“鹤”等都是将抽象的卦辞、卦画转化成的具有生命的形象。又如“命王良掌策驷兮,逾高阁之锵锵。建罔车之幕幕兮,猎青林之芒芒。弯威弧之拨剌兮,射嶓冢之封狼。观壁垒于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硠。”其中“王良”、“驷”、“高阁”、“策”、“罔车”、“青林”、“威弧”、“封狼”、“壁垒”、“河鼓”等全是星宿名。作者或用拟人之法,或赋双关之意,将它们转化为具有生命的形象参与远游求索。这可以说是作者创造性地运用并发展了富有民族特色的比兴之法。作者对天地四方的地理、气候特征以及与其相关的神话传说、历史掌故的准确描写和交融吻合,都充分显示出了精通天文、历算、五经、阴阳、机械制作、属辞造赋的作者其博大精深的学识、奇特丰富的想像力及高超娴熟的语言驾驭能力。
其次就是构思的巧妙。这篇大赋采用的是内外双线并行的结构形式。作者以远游为外在线索,依次叙说远游的原因、经过及结局。在文章的主体,即叙说远游的过程中又以梦见木禾为线索。由于所梦木禾生长在昆仑山上,便产生占梦并登览昆仑山的愿望,也就引出了远游天地四方的情节,并使远游之地的转换是那样的自然而然。以梦境的产生及其实现与破释来安排远游的历程,不仅符合当时人们的思维习惯、欣赏兴趣,也使上下四方的远游紧紧联系起来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另外,作者有意安排的三次占卜也是别具匠心的。其一,三次占卜不仅预示了远游的经历及结局,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使文章的结构更为严谨周密。其二,大凡人们在无力左右自身,无力消除痛苦之时才去求神问卜,故占卜行为本身也从侧面表现出黑暗势力的强大,个人力量的软弱及其内心痛苦的程度。其三,巧妙借助占卜之词表现心灵斗争的另一个侧面,抒发牢骚,流露逃逸意象,流露对昏君阉党的不满。借他人之口说自己要说的话,既委婉,又尽意;既不留把柄,又不失君臣之义;既“言之者无罪”,又“闻之者足以戒”。其四,占卜之词也使其文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增强了诱人的力量。
文章的内在线索则是作者心灵矛盾斗争的运动历程。从纵向上看:先述忠情,这是扬,是主观情志的高扬;再叙忠而受谤的孤独苦闷,这是抑,是客观打击造成的压抑;再叙上天入地的求索,则又是扬,每一次求索的开始都是充满希望的高扬;而每一次求索的失败再度陷入苦闷则又是抑,是希望破灭的压抑;登上昆仑山,神态高驰,这又是扬,是幻想中的高扬;但当他瞥见故土,燃起归乡之情时,这又是抑,是思乡退隐的压抑;回落故乡之后,又高唱着“回志朅来从玄諆,获我所求夫何恩!”这又是扬,是在更高层次上作出超然物外的高扬,而这种高扬实际上是压抑的变态。扬抑的交错则展现出作者心灵运动的发展曲线。从横断面上看:每一断面又充满着心灵的矛盾斗争:忠君与怨君,独立不迁与顺从时俗,进取与退隐,去国与恋土……,作者的战斗冲动与逃逸意象始终交织一处,构成了作者心灵运动的具体内容。
倚天绝壁,直下江千尺。天际两蛾凝黛,愁与恨,几时极? 怒两风正急,酒醒闻塞笛。试问谪仙何处?青山外,远烟碧。
该词为登蛾眉亭远望,因景生情而作。风格豪放,气魄恢宏。
蛾眉亭,在当涂县(今安徽境),傍牛渚山而立,因前有东梁山,西梁山夹江对峙和蛾眉而得名。牛渚山,又名牛渚圻,面临长江,山势险要,其北部突入江中名采石矶,为古时大江南北重要津渡、军家必争之地。蛾眉亭便建在采石矶上。
上阕以写景为主,情因景生。“倚天绝壁,直下江千尺”起句突兀,险景天成:登上蛾眉亭凭栏望远,只见牛渚山峭壁如削、倚天而立,上有飞瀑千尺悬空奔流,泻入滔滔长江。词人见奇景而顿生豪情,“天际两蛾凝黛,愁与恨,几时极”,前句是说:那江天之外两座夹江而立的远山,宛如美人刚刚用黛石涂过的两抹弯弯的蛾眉。“凝”,谓凝止、聚积;在这里则指蛾眉凝愁;这便引出下面的句子“愁与恨,几时极”来,“极”谓极尽、完了:那眉梢眉尖凝聚不解的愁与恨,到什么时候才能消散?这里运用了拟人化与比喻相结合的手法,,说的是蛾眉含愁带恨,其实发泄的却是词人内心的忧国忧民的愁苦。词人生于宋、金交兵、战火遍地的动乱年代,身为南宋官员,面对半壁大好河山已陷金人之手、南宋王朝偏安江南一隅的情景,他所愁所恨的应是对恢复版图、统一旧时河山的希冀一次次的破灭与继续企求。
下阕以抒情为主,情与景融。“怒两风正急,酒醒闻塞笛”是写:波涛汹涌的江水正卷起连天怒两,浪高风急;酒意初退,耳畔便仿佛响起如怨如诉、不绝如缕的塞外悲笛。“塞笛”,自然是边塞亦即“塞外”的笛音;古人以长城为塞,“塞外”则指今长城以外亦即我北部边疆地区,它常与“江南”相对仗使用。身在南国的词人所听到的“塞笛”,只能是因为日夜将收复失地萦绕心头而形成的一种幻觉,在写作技巧上则是使用了跨越空间、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大胆联想,这使豪气之中多少带进了一丝苍凉。当然,“塞笛”也可指实边防军队里吹奏的笛声,因为那时的采石矶就是南宋与金国交界的军事重镇,史载:绍兴三十一年(1161),宋将虞允文曾大败金兵于此地。但诗词贵虚不贵实,若作前者理解,更增加些促人深思的、奇异的色彩。接下来词人又迅速将驰骋的想象拉回到眼前,这里正是唐代大诗人李白晚年颠沛、依傍从叔当涂县令李阳冰生活的地方,采石矶一带正是诗人醉后入水、欲捕明月而葬身的地方。“试问谪仙何处?青山外,远烟碧”中,前句是说:试问到哪里去才能追寻到谪仙人李白的踪迹?作者对着茫茫江水,呼唤寻找着前朝那位狂放不羁、才华横溢的伟大诗人。此时此地,此景此情,这寻找、这呼唤,既是对所倾心仰慕的诗人的凭吊(据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公墓志》记载,李白墓在当涂东南之青山北麓),却也可理解为词人在积极地为苦闷心情寻找寄托,希望自身也具有旷达、豪迈如李白般的性格。结句“青山外,远烟碧”意境开阔,它不仅对前面之问句作了答复,而且是词人对愁与恨交错缠绕所作的奋力摆脱:那万重青山外,千里烟波的尽头、郁郁葱葱的地方,当更有令人神驰的景物。
这是一首托物言志的咏物诗,表面上歌颂橘树,实际是诗人对自己理想和人格的表白。全诗可分两部分,前十六句为第一部分,缘情咏物,重在描述橘树俊逸动人的外美,以描写为主;后半部分缘物抒情,转入对橘树内在精神的热情讴歌,以抒情为主。两部分各有侧重,而又互相勾连,融为一体。诗人以四言的形式,用拟人的手法塑造了橘树的美好形象,从各个侧面描绘和赞颂橘树,借以表达自己追求美好品质和理想的坚定意志。
第一部分重在描述橘树俊逸动人的外美。
开笔“后皇嘉树,橘徕服兮”等三句就不同凡响:一树坚挺的绿橘,突然升立在广袤的天地之间,它深深扎根于“南国”之土,任凭什么力量也无法使之迁徙。那凌空而立的意气,“受命不迁”的坚毅神采,顿令读者升起无限敬意。橘树是可敬的,同时又俊美可亲。
诗人接着以精工的笔致,勾勒它充满生机的纷披“绿叶”,晕染它雪花般蓬勃开放的“素荣”;它的层层枝叶间虽也长有“剡棘”,但那只是为了防范外来的侵害;它所贡献给世人的,却有“精色内白”,光采照人的无数“圆果”。屈原笔下的南国之橘,正是如此“纷緼宜修”,如此堪托大任。这节虽以描绘为主,但从字里行间,人们却可强烈地感受到,诗人对祖国“嘉树”的一派自豪、赞美之情。
此诗第二部分,即从对橘树的外美描绘,转入对它内在精神的热情讴歌。屈原在《离骚》中,曾以“羌无实而容长”(外表好看,却无美好的内质),表达过对“兰”“椒”(喻指执掌朝政的谗佞之臣)等辈“委其美而从俗”的鄙弃。橘树却不是如此。它年岁虽少,即已抱定了“独立不迁”的坚定志向;它长成以后,更是“横而不流”“淑离不淫”,表现出梗然坚挺的高风亮节;纵然面临百花“并谢”的岁暮,它也依然郁郁葱葱,决不肯向凛寒屈服。
诗中的“愿岁并谢,与长友兮”一句,乃是沟通“物我”的神来之笔:它在颂橘中突然揽入诗人自己,并愿与橘树长相为友,面对严峻的岁月,这便顿使傲霜斗雪的橘树形象,与遭谗被废、不改操守的屈原自己叠印在了一起。而后思接千载,以“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收结,全诗境界就一下得到了升华——在两位古今志士的遥相辉映中,前文所赞美的橘树精神,便全都流转、汇聚,成了身处逆境、不改操守的伟大志士精神之象征,而高高映印在历史天幕之上。
本诗借物抒志,以物写人,既沟通物我,又融汇古今,由此造出了清人林云铭所赞扬的“看来两段中句句是颂橘,句句不是颂橘,但见(屈)原与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镜花水月之妙”(《楚辞灯》)的奇特境界。从此以后,南国之橘便蕴含了志士仁人“独立不迁”、热爱祖国的丰富文化内涵,而永远为人们所歌咏和效法了。这一独特的贡献,仅属于屈原,所以宋刘辰翁又称屈原为千古“咏物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