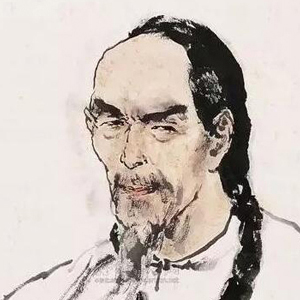这是诗人会试下第,从京城返家,途中题壁之作。诗人感叹科举考试的艰辛,以及饱食终日的当权者不知道朝廷已日薄西山,危机四伏,却依然迷恋着昔日的余晖,因而说出就此归隐,与美人佛经相伴,了此一生的激愤语。诗中既表现了诗人科场失意的愤懑,也流露出对国事时势的深切忧虑。全诗以比喻象征手法刻画社会现实,将个人遭际与国家命运融为一体,深沉蕴藉,耐人寻味。
首联回顾亲身经历的两次科举考试的失败,诗人禁不住发出一声浩叹,这浩叹正如晏殊所谓“劝君看取利名场,今古梦茫茫”(《喜迁莺·花不尽》)的怅惘失望。但是,他并没有因失败而一并失去自信。他相信自己的学问、见识都是独步一时、自成一家的。而也许正因为是“自一家”,他才屡次落第。“莽无涯”三字把时间延伸到遥远的未来,含有无限的感慨,沉痛低徊;“纵横”则又把时间向历史深处推溯再向未来延伸,同时又把现在的一段拓宽,大有纵观古往今来、横视天下当代的气概,充满自信,深沉坚定。这两句一果一因,一叹一转,已经蕴含了全诗的大意。
颔联是全诗的警句,表面是描写此时此地所见的景与物:秋天来了,堂内的燕子还安卧不动;暮色苍茫,路旁的乌鸦依然痴恋夕阳而不归巢。实际上,只要稍微联系一下当时的社会背景,就不难发现这两句诗所隐含的深层意义,那时的清王朝正是处在这样―种秋风衰飒、暮色浓重的局势中,眼看着就有被吞没被覆亡的危险,诗人一路上或许就有许多这样的见闻。而全国上下仍像堂内燕、路旁鸦一样,还沉浸在自我陶醉之中。燕子是候鸟,秋冬之际必须南迁,否则,北方的冬天将冻结它的生命;乌鸦也得在天黑之前归巢,否则将遭遇“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曹操《短歌行二首·其一》)的难堪。而诗人笔下的燕和鸦,居然感受不到秋风、暮气的侵袭,感受不到冬天黑暗死亡覆没的气息,由此引发了诗人的哀叹、焦虑。“夕阳”“暮鸦”意象常见于古诗词中,确有实写景物之义,但这里的“夕阳”应该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乐游原》)一类,与“秋气”一起,成为王朝渐趋衰落的象征。这是诗人的深忧,也是他作为政治家的敏锐,先觉者的悲哀,“自一家”的具体表现。
颈联这两句意思比较晦涩、模糊,大意是说:天生丽质而不愿以姿容媚俗的绝色女子,是得不到人的宠爱的;根底深厚而不能绽开鲜花笑脸迎人的参天古木,也不会得到众眼的赏睐。“东邻”“嫠老”似合用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中“天下之佳人……莫若臣东家之子”及《左传·昭公二十四年》中“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等典故,却又难以指实。这样就导致对诗句的理解产生一定的分歧。“东邻嫠老”“古木根深”作感慨解可,作自负解也可;“难为妾”“不似花”作伤心语可,作矜持语也可;就主体言,作诗人的自道看可,作为对方设看也可。联系全诗及其创作背景,应该说,这些理解都是可以成立的,而只有同时并存才是较为合理的解释。诗人才华出众,思想敏锐,“常为大国忧”,但因为不愿趋时媚俗,得不到世人的理解和赏识,一再落第。现在面对周仪暐这个理解他的人,其内心活动的复杂是可以想见的,自伤自负、自怜怜人,种种情感交结一起,难分先后主次。这两句照应开头两句,是全诗所有情结的绾合。
尾联是说诗人想望着有朝一日像飞鸿那样高翔远翥,退出名利场的追逐,伴着美人和佛经,度过自己的一生。“何日”是一种期盼的口吻,而“葬”则语含酸痛。冥鸿遂迹,美人经卷,似带着一定的哲理和玄义,予人某种启迪,但同样扑朔迷离,难以指实。这两句自是愤激话。其实,由唐至清一千余年有关科举的诗中,最不能当真的就是落第诗的结尾两句。不管它是怎样的激昂慷慨,还是怎样的意志消沉,都只是一时冲动。拿龚自珍来说,虽然从这一年开始他“收狂向禅”,但并未真的一生礼佛成为高僧,况美人与经卷也是难以同时捧置在手的。这一次失败后他又多次赴举,直至一第,也并未真的“鸿飞冥冥”成为世外高人。这是他的矛盾和不幸,也是时代的悲剧。在“秋气”“夕阳”中,他空有救时扶世而“自一家”的心与才,却没有施展怀抱的时与世。他预感到“堂内燕”“路旁鸦”的危险,却只能希望像“冥鸿”那样独自离开,这也正是那个时代“先觉者”的写照。
这篇赋带有明显的寓言性质,它假托“白发”与其主人的对话来构成全篇,抒发了怀才不遇的愤懑,对不重真才实学、只看外表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这篇赋语言朴素,寓言深刻,托讽味长,形式别具一格。
这篇赋表面上的意思比较好理解:当世用年轻之士,年长者无用,作者对此有怨,用了曲折表现的手法,借白发之言说出。但这还不是本篇要揭示的实质问题。赋中说:“贾生自以良才蝇异”,“四皓佐汉,汉德光明。”无论年少、年老,都应以德、才作为录用升迁的标准。所以赋的后一部分说:“曩贵耆耄,今薄旧齿……虽有二毛,河清难俟。”这与赵壹《刺世疾邪赋》中所说“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的意思一致。
左思生活的时代门阀制度森严,政治腐败,左思出身寒门,故一直受压抑而不得展其怀抱。“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是当时的普遍状况。所以这篇看来诙谐的游戏之笔,实是基于作者辛酸经历之上的愤慨之作,只是表现得含蓄隐晦,鉴于种种原因,不便明言罢了。
这篇小赋语言朴素,行文幽默,形式别具一格,乃是在六朝抒情短赋中别具一格的作品。
乾元元年(758)李白流放夜郎(治所在今贵州正安西北),二年春行至巫山遇赦,回到江陵。杜甫远在北方,只闻李白流放,不知已被赦还,忧思拳拳,久而成梦。
这两首记梦诗,分别按梦前、梦中、梦后叙写,依清人仇兆鳌说,两篇都以四、六、六行分层,所谓“一头两脚体”(见《杜少陵集详注》卷七。本篇文字亦依仇本。)上篇写初次梦见李白时的心理,表现对故人吉凶生死的关切;下篇写梦中所见李白的形象,抒写对故人悲惨遭遇的同情。
“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诗要写梦,先言别:未言别,先说死,以死别衬托生别,极写李白流放绝域、久无音讯在诗人心中造成的苦痛。开头便如阴风骤起,吹来一片弥漫全诗的悲怆气氛。
“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不说梦见故人,而说故人入;而故人所以入梦,又是有感于诗人的长久思念,写出李白幻影在梦中倏忽而现的情景,也表现了诗人乍见故人的喜悦和欣慰。但这欣喜只不过一剎那,转念之间便觉不对了:“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你既累系于江南瘴疠之乡,怎么就能插翅飞出罗网,千里迢迢来到我身边呢?联想世间关于李白下落的种种不祥的传闻,诗人不禁暗暗思忖:莫非他真的死了?眼前的他是生魂还是死魂?路远难测啊!乍见而喜,转念而疑,继而生出深深地忧虑和恐惧,诗人对自己梦幻心理的刻画,是十分细腻逼真的。
“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梦归魂去,诗人依然思量不已:故人魂魄,星夜从江南而来,又星夜自秦州而返,来时要飞越南方青郁郁的千里枫林,归去要渡过秦陇黑沉沉的万丈关塞,多么遥远,多么艰辛,而且是孤零零的一个。“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在满屋明晃晃的月光里面,诗人忽又觉得李白那憔悴的容颜依稀尚在,凝神细辨,才知是一种朦胧的错觉。想到故人魂魄一路归去,夜又深,路又远,江湖之间,风涛险恶,诗人内心祝告着、叮咛着:“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这惊骇可怖的景象,正好是李白险恶处境的象征;这惴惴不安的祈祷,体现着诗人对故人命运的殷忧。这里,用了两处有关屈原的典故。“魂来枫林青”,出自《楚辞・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旧说系宋玉为招屈原之魂而作。“蛟龙”一语见于梁吴均《续齐谐记》:东汉初年,有人在长沙见到一个自称屈原的人,听他说:“吾尝见祭甚盛,然为蛟龙所苦。”通过用典将李白与屈原联系起来,不但突出了李白命运的悲剧色彩,而且表示着杜甫对李白的称许和崇敬。
上篇所写是诗人初次梦见李白的情景,此后数夜,又连续出现类似的梦境,于是诗人又有下篇的咏叹。
这是一首咏物诗。前两句写石点题。“虎踞龙蹲”既是写石,又是用典。以“龙蹲”代孔子,用“虎踞龙蹲”形容非常之人,才华之士,在唐人的作品中常可见到。如卢照邻《南阳公主集序》:“龙蹲东鲁,陈礼乐而救苍生;虎踞西秦,焚诗书以愚黔首。”李商隐在这里借以描绘石积于地,辨其姿态,如虎伏欲跃,如龙卧欲飞,以暗示有志于世的才士。而“纵复横”三字则陡转急下,尽写虎石翻仰、龙石横陈的一片散落凋零,紧扣题目中的“乱”字,点出才士失志受挫之意。联系到《易·乾卦》中的“云从龙,风从虎”,更令人有志士沦落之感。“星光渐减雨痕生”一句也为用典。古人以为,地上之石,本天上之星,故《黄石公》曰:“石者,星质也。”《左传》以“陨星”解释“陨石”,并且有“夜中,星陨如雨”的记载。此处以陨星紧扣题目中的“石”字,并以天落之星来暗示才士不凡,回应上句中的“虎踞龙蹲”。然而,星堕人间,光采渐渐泯灭;雨水浸渍,又留下了道道深痕。这是艰难世道、无情风雨刻下的印迹,这是历经沦贱艰虞的生活标识。这两句的含意有四层:一谓石乃陨星,本质不凡;二谓落地化石,星光泯灭,遭际不幸;三谓石形如龙似虎,雄姿依稀;四谓纵横散乱,风雨剥蚀,饱尝艰难;层层转进,于写石之中寄寓了诗人的坎坷不平之志。
诗的后两句因石而寄慨。阮步兵(阮籍)生当魏晋鼎革之际,社会现实的混乱动荡,政治斗争的血腥杀戮,使他非但才志不得施展,而又时有生命之忧,内心痛苦万状。《晋书》记载,阮籍不与世事,酣饮为常(实亦借酒避祸)。闻步兵厨营人善酿酒,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又常醉意驾车,不由路径,至不可行处,便恸哭而返。李商隐此处就是用阮籍之事以抒发自己的穷途之悲。“不须并碍东西路,哭杀厨头阮步兵。”即是说,星落光灭,散乱纵横,又加以雨痕水渍,使人观此石便已有世事险恶、人生唯艰之痛,根本不用像阮籍一样驾车寻路、至行不通时方悲途穷。这样的表达方式,比直说自己有阮籍穷途之悲更沉痛,而且纤徐委婉,耐人寻味。纪昀评此诗,曾谓冠阮籍以“厨头”,语言“粗鄙”、“不佳”(见《李义山诗集辑评》)。其实,阮籍名为求官,实为求酒,至官之日,便与刘伶痛饮。酒乃厨头所酿,称他为“厨头”,是以讥讽的笔调写阮籍的无可奈何的悲哀,又是借阮籍为“厨头”抒发自己的才志不得其所的悲愤。这也是李商隐诗的语意曲折之处。
想要真正理解像李商隐这样喜用僻典、情思幽微的诗人的作品,就要注意分辨那透过客观物象以传达主观情怀的信号。《乱石》一诗,各注家说法不一:或以为是讥刺令狐绹,或以为是愤怨仕途不通,或以为是痛恨小人蔽贤;但莫不以诗中之石为阻碍路途的劣物。此意均由题目中的“乱”字生出。但是,“乱”本形容石落散乱之态,并非指石本身;以陨星指小人,也不符合古典诗歌的表达习惯;诗曰“光渐灭”、“雨痕生”义分明寄同情于陨石。而且,如果是乱石挡路,诗人就不必说“不须并碍东西路”了。可见诗中写石并不从“挡路”着眼。正因为那弃置散落、风雨侵蚀的星石的形象已凝聚了多重才士失志受挫的含意,所以引起屡试不第、沉沦漂泊的诗人的共鸣。“不须”二字,尤见悲愤。
这首诗咏石而有穷途之悲,悲石之命运与己之不幸相同,悲石只为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