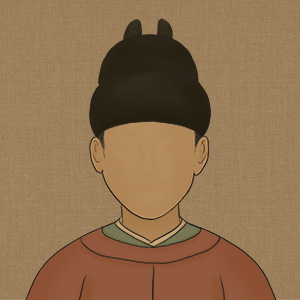巢乾燕乳虫供哺,花过蜂闲蜜满房。
闭户不知春已去,钞书但觉日方长。
所嗟诗思年来减,虚负奚奴古锦囊。
巢乾燕乳虫供哺,花过蜂闲蜜满房。
闭户不知春已去,钞书但觉日方长。
所嗟诗思年来减,虚负奚奴古锦囊。
此诗前四句开门见山亮出矛盾,将龌龊小人与高怀旷士分列两句,形成对照。“小人自龌龊”构成全诗主脑,是后文穷形极相描绘的张本。在这两句写实诗前用“蓼虫避葵堇,习苦不言非”两句来起兴,既有含义,又增添了文学情趣。蓼虫习惯了辛辣苦味,不喜欢堇葵的甘甜。这两句不仅是兴,而且也是比。其比的含义,前人或谓是指小人不知旷士之怀,犹如蓼虫不知葵堇之美;或谓是指旷士习惯于辛苦生涯,不以辛苦为非。细绎诗意,当以后说为是,因为“避”、“不言非”等语,并无贬义,而以苦为乐,从来就是豁达放旷之士的本色;只有小人,才是趋甘避苦之徒。
从“鸡鸣人城里”至“钟鸣犹未归”八句是此诗第二层,写“小人”的龌龊行为。“鸡鸣”“平旦”“日中”“钟鸣”是贯串八句的时间线索。其人物则是“冠盖”,他们的一天,从“平旦”起,天子的“禁门”刚刚打开,就蜂拥而至了。“纵横至”、“四方来”,来势汹涌如潮水,笔端带有揶揄调侃之意。乘他们车马驰骤之际,诗人迅速为他们的风尘尊容勾勒了一幅生动无比的漫画:“素带曳长飙,华缨结远埃。”这些颇有身分的人,他们的素带在急驰的大风中乱飘,华丽的帽缨上结聚了远道而来的尘埃。这幅画有色彩,有动态,有细节,形象传神,耐人品味。句中未著一字褒贬,却“写尽富贵人尘俗之状”(沈德潜《古诗源》),把角逐名利场者的丑态刻划得入木三分,不愧为神来之笔。他们到处奔竞,“日中”不可能会停止钻营。就连夜深“钟鸣”后他们犹未回家。一个“犹”字,有多少惊讶、感叹、挖苦之意。后汉安帝《禁夜行诏》云:“钟鸣漏尽,人阳城中不得有行者。”这里说“钟鸣未归”,可见奔竞日盛,古风荡然无存。
“夷世不可逢”以下是此诗第三层,记录了奔竞小人对道旁旷士的谈话,他们对旷士说道:现在是千载难逢的太平盛世,君王也是真正爱才的贤君。他英明的考虑出于自己的判断,不受任何外来影响而猜疑动摇。这些正经话出自小人之口,就显得肉麻阿谀与不伦不类,因而具有极大的讽刺性。接着,小人们又向旷士津津乐道地夸说起了进入仕途的容易和当官的好处。这四句是说才能之士只要有一言之美,片善之长,就会受贤君青睐,被封官赐爵,辞别田野,登上朝堂。而贤君爱才,岂但只赏赐白璧,还将仿效燕昭王筑黄金台来重金招聘你们呢。这四句虽是小人们的劝诱、夸说之辞,但也是他们一心只想升官发财的灵魂大曝光,写得真是笔锋辛辣,利如刀锥。“今君有何疾,临路独迟回?”最后,小人以嘲弄的口吻诘问旷士:你到底有什么毛病,竟面对阳关大道还独自徘徊不前?全诗至此顿住。对于无耻小人的挑衅,诗人没有也不屑回答,但不回答并不等于没有答案。读者若试着掩卷思索,就会发现,答案已在开头“小人自龌龊,安知旷士怀”之中了。这一结回应开头,使通篇皆活,旷士形象虽未著墨,但在对照中自显出其迥异小人的品格。这个结尾让应受嘲弄的人去厚颜嘲弄别人,真是幽默滑稽而有波澜,可谓味蕴言外,冷峻隽永。
《代放歌行》在《乐府诗集》中属《相和歌辞·瑟调曲》。《歌录》曰:“《孤生子行》,亦曰《放歌行》。”《孤生子行》,又题作《孤儿行》,在乐府古辞中写的是孤儿备受兄嫂折磨,难与久居的内容。鲍照的拟作,旧瓶装新酒,用以揭露黑暗,抨击时政,大大拓宽和加深了这一乐府旧题的表现力。在这个方面,也同样显示了诗人非凡的艺术勇气和独辟蹊径的创新精神。
这是一个古老的传说:帝尧曾经将两个女儿(长曰娥皇、次曰女英)嫁给舜。舜南巡,死于苍梧之野。二妃溺于湘江,神游洞庭之渊,出入潇湘之浦。这个传说,使得潇湘洞庭一带似乎几千年来一在被悲剧气氛笼罩着,“远别离,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海水在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一提到这些诗句,人们心理上都会被唤起一种凄迷的感受。那流不尽的清清的潇湘之水,那浩淼的洞庭,那似乎经常出没在潇湘云水间的两位帝子,那被她们眼泪所染成的斑竹,都会一一浮现在脑海里。所以,诗人在点出潇湘、二妃之后发问:“谁人不言此离苦?”就立即能获得读者强烈的感情共鸣。
接着,承接上文渲染潇湘一带的景物:太阳惨淡无光,云天晦暗,猩猩在烟雨中啼叫,鬼魅在呼唤着风雨。但接以“我纵言之将何补”一句,却又让人感到不是单纯写景了。阴云蔽日,那“日惨惨兮云冥冥”,就像是说皇帝昏聩、政局阴暗。“猩猩啼烟兮鬼啸雨”,正像大风暴到来之前的群魔乱舞。而对于这一切,一个连一官半职都没有的诗人,即使说了,也无补于世,没有谁能听得进去。既然“日惨惨”、“云冥冥”,那么朝廷就不能区分忠奸。所以诗人接着写道:我觉得皇天恐怕不能照察我的忠心,相反,雷声殷殷,又响又密,好像正在对我发怒呢。这雷声是指朝廷上某些有权势的人的威吓,但与上面“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相呼应,又像是仍然在写潇湘洞庭一带风雨到来前的景象,使人不觉其确指现实。
“尧舜当之亦禅禹,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这段议论性很强,很像在追述造成别离的原因:奸邪当道,国运堪忧。君主用臣如果失当,大权旁落,就会像龙化为可怜的鱼类,而把权力窃取到手的野心家,则会像鼠一样变成吃人的猛虎。当此之际,就是尧亦得禅舜,舜亦得禅禹。诗人说:不要以为我的话是危言耸听、亵渎人们心目中神圣的上古三代,证之典籍,确有尧被秘密囚禁,舜野死蛮荒之说啊。《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载:尧年老德衰为舜所囚。《国语·鲁语》:“舜勤民事而野死。”由于忧念国事,诗人观察历史自然别具一副眼光:尧幽囚、舜野死之说,大概都与失权有关吧?“九疑联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舜的眼珠有两个瞳孔,人称重华。传说他死在湘南的九嶷山,但九座山峰联绵相似,究竟何处是重华的葬身之地呢?称舜墓为“孤坟”,并且叹息死后连坟地都不能为后人确切知道,更显凄凉。不是死得暧昧,不至于如此。娥皇、女英二位帝子,在绿云般的丛竹间哭泣,哭声随风波远逝,去而无应。“见苍梧之深山”,着一“深”字,令人可以想象群山迷茫,即使二妃远望也不知其所,这就把悲剧更加深了一步。“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斑竹上的泪痕,乃二妃所洒,苍梧山应该是不会有崩倒之日,湘水也不会有涸绝之时,二妃的眼泪自然没有止期。这个悲剧实在是太深了。
诗所写的是二妃的别离,但“我纵言之将何补”一类话,分明显出诗人是对现实政治有所感而发的。所谓“君失臣”、“权归臣”是天宝后期政治危机中突出的标志,并且是李白当时心中最为忧念的一端。元代萧士赟认为玄宗晚年贪图享乐,荒废朝政,把政事交给李林甫、杨国忠,边防交给安禄山、哥舒翰,“太白熟观时事,欲言则惧祸及己,不得已而形之诗,聊以致其爱君忧国之志。所谓皇英之事,特借指耳。”这种说法是可信的。李白之所以要危言尧舜之事,意思大概是要强调人君如果失权,即使是圣哲也难保社稷妻子。后来在马嵬事变中,玄宗和杨贵妃演出一场远别离的惨剧,可以说是正好被李白言中了。
诗写得迷离惝恍,但又不乏要把迷阵挑开一点缝隙的笔墨。“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雷凭凭兮欲吼怒。”这些话很像他在《梁甫吟》中所说的“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轰震天鼓。……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不过,《梁甫吟》是在说,而《远别离》中的这几句隐隐呈现在重重迷雾之中,一方面起着点醒读者的作用,一方面又是在述及造成远别离的原因时,自然地带出的。诗仍以叙述二妃别离之苦开始,以二妃恸哭远望终结,让悲剧故事笼括全篇,保持了艺术上的完整性。
诗人是明明有许多话急于要讲的。但他知道即使是把喉咙喊破了,也决不会使唐玄宗醒悟,真是“言之何补”。况且诗人自己也心绪如麻,不想说,但又不忍不说。因此,写诗的时候不免若断若续,似吞似吐。范梈说:“此篇最有楚人风。所贵乎楚言者,断如复断,乱如复乱,而辞意反复行于其间者,实未尝断而乱也;使人一唱三叹,而有遗音。”(据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转引)这是很精到的见解。诗人把他的情绪,采用楚歌和骚体的手法表现出来,使得断和续、吞和吐、隐和显,消魂般的凄迷和预言式的清醒,紧紧结合在一起,构成深邃的意境和强大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