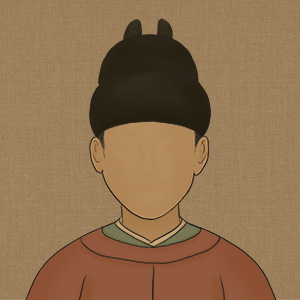从此诗所表达的情绪与景物看,此诗应该作于安史之乱以后,贬低遍地烽火一片狼籍,不象是此前所作,没有那样的景遇。但是,安史之乱以后,李白已经到了江南,在江西九江一带。李白的子女却阻隔在曲阜那一带,因为当时李白的田地在那里。
所以,很难断定此诗的创作时间,难道又是李白梦游?帝图终冥没:难道指安禄山的失败?那李白叹息的是唐玄宗引起的巨乱?没有早听他的预言?
这首词,正如周济所云:“不过桃花人面,旧曲翻新耳。”(《宋四家词选》)孟棨《本事诗·情感》记崔护于清明在长安城南村庄艳遇故事,作诗云:“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再结合周邦彦的身世和政治生涯来看,词中的“刘郎”当系以自己比刘禹锡而言。刘禹锡是唐代顺宗时的革新派人物,后遭贬放,又曾返京师。写有《再游玄都观绝句》,诗云:“百亩中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周邦彦倾向新政,曾为宋神宗所赏识,后神宗逝世,高太后听政,任用司马光等,周邦彦外出为庐州教授,羁旅荆江,游宦溧水。直至哲宗亲政,罢黜旧党,周邦彦才得返都。但在当时执政的新党实已变质,他的抱负仍然不得抒展,所以这首词当是暗寓这些情节的。
此词,字面上的重见桃花、重访故人,有“还见”、“重道”之喜,但只见“定巢燕子,归来何处”“旧家秋娘,身价如故”,自己则“探春尽是,伤离意绪”。空来空去,落得“断肠院落,一帘风絮”。此词,大开大合,起句突而又平。又其云在“章台路”上,不写眼前所见,却说“还见”云云,梅桃坊陌,寂静如故,燕子飞来,归巢旧处,全系写景,但以“还见”贯之,人之来,人之为怀旧而来,人之徘徊踯躅,都从字里行间露出,景中含情,情更浓烈,可见此词的沉郁处。中片本为双拽头,字句与上片同。以“黯凝伫”之人的痴立沉思写起,不写他所访求之人在与不在,而只“因念”云云,表面上描绘其昔时情态笑貌,实则追想从前的交游欢乐,但不明说,实是词的顿挫之处。下片则铺开来写,加深描绘“前度刘郎”“旧家秋娘”,一则“事与孤鸿去”,一则“声价如故”,对照写来,顿挫生姿。“燕台句”写空有才名,而今只留记诵。“知谁伴,名园露饮,东城闲步”,清游何在?真是沉郁之至。一结以“飞雨”、“风絮”,景中含情,沉郁而又空灵。这首词以“探春尽是,伤离情绪”为主旨,直贯全篇。从时间上说,是以今昔情节对比写来。上片之“章台路”、“坊陌人家”均写今日之景。中片之“因念个人痴小”云云都是写昔人的情况。今日之景是实写,昔日之人是虚拟。一实一虚,空灵深厚。“还见”字犹有过去的影子。“因念”字徒留今天的想象,又是今中有昔,昔中有今。下片则今昔情事交织写来,“前度刘郎重到”有今有昔。“同时歌舞,唯有旧家秋娘,声价如故”,则是昔日有者,今日有存有亡。“吟笺赋笔,犹记燕台句。知谁伴,名园露饮东,东城闲步。”又是昔日之事,而今日看来,一切皆“事与孤鸿去”。最后又写念日情况,是在“官柳低金缕”的风光中,“归骑晚,纤纤池塘飞雨,断肠院落,一帘风絮。”有今而无昔。今之惆怅和昔之游乐成一鲜明对照。词在时间上就是这样似断似续,伤春意绪却是联绵不断。词又是一起写景,一结写景。一起静景,一结动景。花柳风光中人具有无限惆怅,是以美景衬托出感伤,所以极为深厚。加以章法上的实写、虚写、虚实穿插进行,显出变化多端,使这首词极为沉郁顿挫而得到词中之三昧。
一位体态轻盈、艳丽多情的少女,眉目含情,风彩动人。
诗人通过这首小词,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情。全词描写细腻,抒情委婉。自是《香奁集》中之佳作。表现了和凝词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