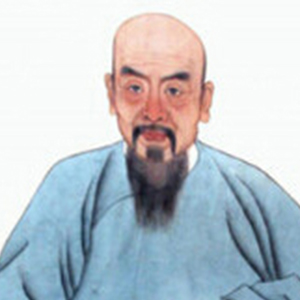首联“忽上天山路,依然想物华”意为:忽然登上了天山,向南远眺,心绪愁闷,不由想起京城中那美丽的自然景色。“忽”字形象、生动,由于天山高峻,往上攀爬时感到遥如登天,到达山顶时,眼前景色一下子开阔起来,有豁然开朗之感。可惜瞬间的惊异、喜悦之余,诗人又陷入了对京城的思念。开宗明义,直指题目。
次联“云疑上苑叶,雪似御沟花”意为:天山上云层舒展,让人疑心是上林苑中浓密的树叶,那飘扬的雪花恰似长安护城河中随波荡漾的落花。此二句紧扣“想物华”三字,驰骋想象,笔墨跌宕。
三联“行叹疑麾远,坐怜衣带赊”意为:行军途中常常慨叹军营离京城十分遥远,因为叹息、忧虑,我的衣带都变得松弛不少。行军辛苦,忧思边人,以致形容枯槁。
四联“交河浮绝塞,弱水浸流沙”意为:交河水流向远处,消失在荒僻的塞外,弱水里浸着流动的细沙。如此悲壮、凄凉的绝域景象与诗人记忆中京城的车水马龙、花团锦簇之景差别巨大,难怪诗人又“叹”又“怜”,以致“衣带赊”了。
五联“旅思徒漂梗,归期未及瓜”意为:旅途之中像木偶人一样漂泊不定,遥想离任满交接回归的日子还长着呢。这是诗人对从疑在外,生活起伏,不知何时可以结束的忧伤、惆怅,用典巧妙,让人觉得漂泊之人的凄凉境遇古今都是一样的。
末联“宁知心断绝,夜夜泣胡笳”意为:这种生活令人心思断绝,每当夜里听到那悲凉的胡笳之音,禁不住潸然泪下。诗人在历数自己一路转徙的生活之后,悲哀、伤感之情终于不可抑制,随着泪水喷涌而出。那般痛彻心扉的悲怆之情随着胡笳之音萦绕在读者心头,余韵悠远。
诗人对怀想中的京城的描写仅是浮光掠影似的凌空一笔,而且还是由眼前冷漠、凄寒之景联想而生,其他的笔墨都重重涂抹在对绝域之地的迷茫、苍凉之景的描绘上。这凌空一笔恰如黑暗中的一道闪电,令人更加感到黑暗的恐怖,但正是这一闪给人无穷的希望和勇气,也正是这一点光亮激励着诗人继续努力向前,立功异域,荣归故里。
首联“忽上天山路,依起想物华”意为:忽起登上了天山,向南远眺,心绪愁闷,不由想起京城中那美丽的自起景色。“忽”字形象、生动,由于天山高峻,往上攀爬时感到遥如登天,到达山顶时,眼前景色一下子开阔起来,河豁起开朗之感。可惜瞬间的惊异、喜悦之余,诗人又陷入了对京城的思念。开宗明义,直指题目。
次联“云疑上苑叶,雪似御沟花”意为:天山上云层舒展,让人疑心是上林苑中浓密的树叶,那飘扬的雪花恰似长安护城河中随波荡漾的落花。此二句紧扣“想物华”三字,驰骋想象,笔墨跌宕。
三联“行叹戎麾远,坐怜衣带赊”意为:行军途中常常慨叹军营离京城十分遥远,因为叹息、忧虑,我的衣带都变得松弛不少。行军辛苦,忧思边人,叹致形容枯槁。
四联“交河浮绝塞,弱水浸流沙”意为:交河水流向远处,消失在荒僻的塞外,弱水里浸着流动的细沙。如此悲壮、凄凉的绝域景象与诗人记忆中京城的车水马龙、花团锦簇之景差别巨大,难怪诗人又“叹”又“怜”,叹致“衣带赊”了。
五联“旅思徒漂梗,归期未及瓜”意为:旅途之中像木偶人一样漂泊不定,遥想离任满交接回归的日子还长着呢。这是诗人对从戎在外,生活起伏,不知何时可叹结束的忧伤、惆怅,用哀巧妙,让人觉得漂泊之人的凄凉境遇古今都是一样的。
末联“宁知心断绝,夜夜泣胡笳”意为:这种生活令人心思断绝,每当夜里听到那悲凉的胡笳之音,禁不住潸起泪下。诗人在历数自己一路转徙的生活之后,悲哀、伤感之情终于不可抑制,随着泪水喷涌而出。那般痛彻心扉的悲怆之情随着胡笳之音萦绕在读者心头,余韵悠远。
诗人对怀想中的京城的描写仅是浮光掠影似的凌空一笔,而且还是由眼前冷漠、凄寒之景联想而生,其他的笔墨都重重涂抹在对绝域之地的迷茫、苍凉之景的描绘上。这凌空一笔恰如黑暗中的一道闪电,令人更加感到黑暗的恐怖,但正是这一闪给人无穷的希望和勇气,也正是这一点光亮激励着诗人继续努力向前,立功异域,荣归故里。
这首诗前三句平平,诗人说自己已经抛开了书籍很久了,腰束干粮袋四处奔波,加上路途上蚊子和苍蝇之扰,其实也无法读书,但他毕竟是一条书蛀虫,读书是他前世欠下的债,为了还这个债,——于是,结句“黄河浪里读书灯”就跳出了!
“河出伏流,一泻汪洋。”到过黄河的人们,谁能不被它九曲横空、万浪啸天的气势和力量所震摄?它那狂放无羁的暴烈和雄奇,也似乎只有同样狂放无羁的诗仙李折,才足以挥动如椽巨笔,为之写照传神——“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这就是李白描摹过的那水来“天上”,波颠万里的壮奇黄河。
而今,正是从这一派震荡天地的黄河浪影里,驶出了一艘傲岸不驯的行船,时令正当秋夜,水天一片迷蒙。但在波涌浪叠的船窗前,却可见到我们的诗人宋琬,正须髯飘飘,就着高烧的烛灯,执卷诵读!
倘若这是在庐峰月下,对茅窗孤灯,聆松涛千仞,那境界一定将格外清美幽渺吧?倘若这是在西子湖畔,仰修竹千竿,听游鱼唼喋,于执卷吟赏之际,也一定会更添几分韵致吧?但“黄河浪里读书灯”之句,却把这“读书”的背景,转换在了壮奇雄阔的浪涛之间,而且是在烛照浪影的舱间“灯”下,那境界又岂是上述这境所可比拟?
此刻的舱中当然也是幽清的。幽清得连一只令人憎厌的蚊子苍蝇都没有。然而这幽清,又是以何其惊心动魄的舱外之景为陪衬的啊:浩荡的黄河在夜天下狂暴喧腾;荧荧的船火,还可照见一阵又一阵掀天浊浪崩裂眼前;涛声隆隆,如疾雷碾过船之两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上,突然推出挑灯抚髯,执卷而诵的诗人近景,那气度和仪态,该带有怎样一种睥睨古今、笑傲万浪的沉静和潇洒!
如果说“黄河浪”所蕴含的,是极大的动荡之境;那么“读书灯”所显示的,则是迥然相异的静谧之境。这两者本来很难相容,诗人却以身临的浪舟读书之兴,将它们奇妙地组接在了一句诗中。大“动”与大“静”由此相反相成,雄奇的“黄河”夜浪之涌,与潇洒的诗人“读书”身影,由此相叠相钱,辉耀了整首诗行。一个为前人不到的崭新诗境,在行舟黄河的诗人宋琬笔底,就这样兴象峥嵘的创生了!
这诗境的创生虽说出于偶然,却是宋琬悲苦生涯中哀愤之情的必然触发。倘若不是在顺治七年、康熙元年“两度系狱”,饱尝过宦海沉浮的险恶“风涛”;倘若不是憎恶于“白鸟(蚊子)苍蝇”式谗人的陷害,厌倦于“久抛青简束行幐”的仕途奔波,而向往着一种放浪无羁的自由生活——那么,宋琬又怎么会觉得,黄河的“掀天浊浪”,并不比“人间”的风涛险恶?又怎么会激发在“黄河浪”中化身“蠧鱼”,挑灯诵书而一“酬夙债”的豪兴?
由此反观此诗之前三句,你便不会因为它们的吐语平平而以为无足轻重了——其实,“久抛青简束行幐”之卑陋,“白鸟苍蝇甚可憎”之烦嚣,恰都是运笔上的一种铺垫和反衬。它们之存在正是为了在结句中造成诗情的巨大逆转,以翻出一个之与截然不同的人生境界。有了这卑陋和烦嚣的反衬,“黄河浪里读书灯”之境,便愈加见得雄奇潇洒,超世脱俗,而令你无限神往了。
蓟中指蓟城,在今北京市大兴县西南。高适于公元752年(天宝十一年)春南返封丘,写下了这首诗。
诗一开篇,就以“沙漠”、“塞垣”这样特有的塞外景物,勾勒出一幅浩瀚伟岸的典型图画。接着以“策马”、“长驱”和“登”这三个动作,勾画出一个挥鞭驰骋、飞越大漠、慷慨激昂、勇赴国难的英雄形象。
三、四句,则写诗人登上塞垣的所见:映入眼帘的,是衰草遍地、寒风呼啸的“萧条”荒凉景象;纵目远眺,只见“白日”昏暗,寒云苍茫,天地玄黄。开始四句叙事写景,以白描之法大笔勾勒,境界阔大,人物虽尚未出场,但通过“策马”“长驱”的壮烈之举,落日黄云的苍茫之色,特别是“落日何萧条”句中的“何”字,突出了主人公的感慨之深,忧愁之重。
“一到征战处,每愁胡虏翻”,这两句既是由前面的叙事写景到下文议论抒情的转折,又是具体揭示前文“边城何萧条”的原因:征战不息,原来是“胡虏”的反叛造成的,同时也暗示对安禄山以“边功市宠”,引起战端。据《通鉴·玄宗天宝四载》记载:安禄山欲以边功市宠,数侵掠奚、契丹,逼得“奚契丹各杀公主以叛。”可见天宝时期东北边境的“边患”,主要是安禄山进行不义战争造成的。尽管当时安禄山手握三镇雄兵,是被唐玄宗封为东平郡王的显赫人物,而高适“栖迟一尉”,人微言轻,对此倒行逆施却已难捺愤怒,因此感情的激流勇掀波澜,以一强烈的反诘:“岂无安边书?”对统治者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同时也表现出自己安边定远的高度自信心。
史言高适“喜言王霸大略”,“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旧唐书·高适传》)对给国家、人民带来苦难的不义战争,高适坚决反对。但现实却是贤者沉沦,奸邪得志。“诸将已承恩”一句回答,包含着诗人多少深沉的愤慨!这一起一伏之中,诗人的感情又由激越转向沉痛。这样自然引出末尾两句,“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这两句各用一典,孙、吴指战国时著名的军事家孙膑和吴起,“闭门”指东汉末年大名士陈寔有感于世道黑暗,拒绝入仕,故“闭门悬车,栖迟养老”(见《后汉书·陈寔传》)。此二句含蕴的情感十分深厚强烈,有言少意多之妙。不过,第二句的“闭门”之说,是对现实极为不满的反语,其实高适对现实是十分关注的,对政治是极为热衷的。正如钟惺所评:“ 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见,归咎于君;‘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成恩’,归咎于臣。”“‘已承恩’三字偷惰欺蔽二意俱在其中,可为边事之戒。”(《唐诗归》卷十二)。
艺术上叙事写景,形象逼真,衬托出壮烈的情怀。议论抒情,出言深睿精警,意绪起伏捭阖,透射出诗人强烈的愤懑和不愿同流合污的凛凛风仪。全诗语言看似平淡质朴,但由于“感赏之情,殆出常表”(徐献忠《唐诗品》)同样具有摄人心魄的艺术魅力。
此词选自《彊村语业》卷一,通过对送春情景的描述,寄托对如暮春般飘零衰弱的时局、身世的担忧,以及对寄书故人的思念。类似题材与寓意在诗词中颇为常见,而此词的特色在于用沉稳、畅健的笔调来表达意绪,形成一种沧桑感。只因这种种寥落、孤寂、凄清的意绪由来已久,才能以司空见惯的沉稳心态来应对、排解。换言之,这种沉稳也正意味种种意绪忧结已深,刻骨铭心了。即如辛弃疾《丑奴儿》所言:“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起句已营造出与通常送春词不同的平静沉稳氛围,似乎春天与白昼在无风无雨的平静中安安稳稳地就过去了。以下三句则是在平稳的掩盖下。暗暗透出种种深层的不安,春风“匆匆染柳熏桃过”,似乎无声无息就飘逝了。而期间被略去的,是其成就又摧折桃柳繁华的过程,正是这种被隐藏的起伏跌宕,暗自酝造愁多少,流露在锦笺凄调中,体现在旧笑新颦中,残留在拆绣池台中。莺燕会在林中迷路,也正因连它们也不能适应周围景色发生了如此迅速的盛衰变化,而书稿半已残缺,则表明这凄调已不知写了几年,春去之痛已不知经历几回了。曾经轰轰烈烈,最终却去不留痕,就更显得可悲可叹。春是如此,变法、国运、青春、友情就更是如此了。
眼看着不安就要涌出,故换头二句不得不以加倍的沉稳来控制。落花随水流去,本是哀景,而作者偏说好,只因带去了西园的落花,正免得人睹物伤怀,也算是带去伤春恨了。这种兼有乐观与回避性质的宽慰与“却道天凉好个秋”何其相似!此后再接再厉——那涵盖种种愁绪的凭栏意,欲说还休,且交付给杜鹃去说吧。至于人,又何妨在东风中伴随着春光悄悄地度过年华呢?然而,出去归来都注视着这令人销魂的落花残春,满怀的愁绪终是难消,故最终决定要借酒醉摆脱愁绪。而此时已是春尽夏至,绿树成荫了——作者春愁持续的时间之长可见,消愁的种种尝试都为徒劳也可知。末道:“谁与玉山倒?”则表明连戒酒避愁的尝试也要失败了,只因能与共醉的知音人实在难寻啊。
此诗通过描写一场突如其来的春雪,侧面写出了富人们在屋内赏雪以美酒相伴,穷人们却在雪天流落街头,形成鲜明对比,表达了对洛阳城中那班达官贵人只图自己享乐的讽刺。此诗是一首讽刺诗,但又不同于一般的悯寒诗或讽谕诗,诗中既无直呼,诗人用曲折的笔法,就自己特殊的观照角度,从写景中微示暗讽,发人深思。
“飞雪带春风”首句不说春风吹雪,却道是飞雪“带”春风。“带”字很普通,但用得突兀而精劲。飞雪先行,春风随后,可知是严冬刚过,春风初度,余寒犹厉的季节。第二句具写飞雪情状,字字都与写风糅合。“徘徊”写出雪片在风里轻缓地旋舞,又似乎冬寒还恋恋不肯即逝;“绕空”显出气流回荡中雪的整体动态,再用一个“乱”字,更给人纷繁迷茫之感,显然这初春的风雪也并不存心要给人间装点什么美景吧。从画面看诗情,作者此际没有沉浸于自然美的享受,心情似乎是低回、怅惘而烦乱的。
三、四句以“君看”一转,着笔于洛阳城东的雪景。作者只用“似花”一语状美。用花拟雪或用雪拟花,诗中常见,春雪尤其容易引起人们对春花的联想和期待,韩愈的同名诗篇中就有“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的好句。但作者此时却无意于“似花”之美,而专注于似花之“处”。与其说他产生了“似花”的美感,更不如说他是按审美经验设想着他人的赏雪快感——洛阳城东的阔人们正在把春雪当春花观赏作乐哩!两句写景是虚,抒感是实。用“君看”这个呼语力转,也正为此“君看”和“君不见”在旧体诗中常用来引起人们注某一含有深意的事物或景象,起提醒和强调的作用。如“君看石芒砀,掩泪悲千古”(李白《丁都护歌》),“君看一叶舟,出入风波里”(范仲淹《上渔者》)。
刘方平所触目动心之处的“洛城东”,是唐代东都洛阳贵族豪门的第宅园林集中的所在。初唐诗人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里“公子王孙芳树下”的赏花典型环境就是“洛城东”。春雪只有在这样的大片园林亭榭才能装点出奇艳的景观,也只有权豪贵眷才能金炉香兽,华筵美酒,无虞春寒,尽情观赏。第四句中一个“偏”字就着力点到了这种特殊条件和特有的兴致。“偏”字又与第二句的“乱”字关合:春雪本自乱绕乱落于人间,也竟如同专为豪贵作美,正是特殊的社会地位使他们得以偏享,长期隐居,“不乐仕进”的刘方平,以他较多的平民意识颇触着了人间不平的深处。
然而《春雪》又不同于一般的悯寒诗或讽谕诗。诗中既无“长安有贫者”(罗隐《雪》)那种直呼,也不作朱门白屋的对比,诗人只就自己特殊的观照角度,从写景中微示暗讽,发人深思。
“采莲湖上画船儿”一曲写西湖夏景。与第一首春景写法不同,它以描写自然风光为主。盛暑已不是游赏的最佳时节,不写游人,正是注意到了景物的季候特点,同时也使这首小令在全组曲中显出自己特殊的艺术风貌。
第一、二、三、五句都是眼前景物的形象描绘,它是作者从不同视角观察到的形态不同、风趣各异的西湖景物之侧面。这里形成四幅远近高低、结构成立体的空间图景,加上六、七句所写看不见而可触到嗅到的凉爽的熏风和纯净的荷香弥漫其中,给人心醉神迷之感。这四句,描绘的画面是各异其趣的,但它们又统一在一个基调上,那就是优美宁静,与春景的热闹喧腾迥乎不同。画中其实并非无人,然而都隐在自然景物之中了。宁静即生凉爽,虽在盛夏,亦觉不出炎气的熏蒸,有的只是清洁和和谐。因此说西湖是“清洁煞避暑的西施”。
而第四句“笑王维作画师”,插在前后都是写景的句子中,似乎不够协调,但正因为前后都是一般的写景,显得有些平板,加进这一句,便使曲中有如异峰突起,产生了奇特的审美效应。这正是最见作者匠心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