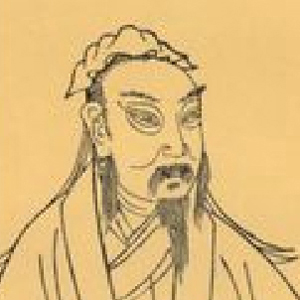这是《花间集》中所收牛峤七首《菩萨蛮》中的一首。所咏虽不出男女之情事,但词中女主人公所念之人身处辽阳(古来为征戍之地),则此词在思想内容方面就非《花间集》中那些纯咏妇女生活及男女情事的作品所可追配的了。
此词语言俊丽,形象鲜明,曲折传情。落花满径,柳絮随风,呢喃双燕,惊扰残梦。这恼人的春色,撩人愁思。这首词描景写人,细腻柔和,宛转多姿,表现了晚唐五代的词风。
上片首句写女主人公服饰之精美。所著既为舞裙,则其为舞妓身份自明。“香”与“暖”写舞裙之精,“金泥凤”写舞裙之美,极生动活脱之趣。服饰之精美如此,则其人之美可见。第二句写梦中惊醒。梦而谓之“残”,说明梦惊做完。至于其所梦的内容,综观全词自可知晓。好梦惊竟而被语燕惊醒,则其恼与怨亦可以想见。此句暗中化用金昌绪“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诗意,但比金诗更加委婉含蓄,实为《花间》本色。画梁之燕呢喃私语又暗形女主人公之孤单寂寞。梦后的一切依然如故:门外柳絮纷飞,而玉郎仍不见归。柳花飞既点明节令为春天(而春季是女子念远之心情最为急切的时候),又暗状女主人公残梦初醒时的迷离恍惚的精神状态。“犹”宇暗逗出一点怨意。
过片首句是承上片末句而来。“匀”字一则表明其非痛哭流涕而是泪水暗滴,将痛苦强忍强咽,苦而必须咽、必须忍,则更见其苦;二则表明其力护容貌之美,故第二句接写其眉:“眉剪春山翠”,意谓双眉被剪画成春山之状,这句是暗用《西京杂记》所说卓文君“眉山如望远山”的典故。第三句“何处是辽阳”,点明“玉郎”所在之地。此问句于无限向往之中渗透着无限哀怨与无可奈何的情绪。此实可问而不可答,故结以“锦屏春昼长”。“长”字固是春昼的实写,也是心理状态的虚写。以景语作结,极迷离动荡之致,给人以无限想象的余地。
这首词在艺术上的特色是欲扬先抑,声情顿挫。词的意旨,原在于刻画女主人公思念征人的情怀。开篇却用高华曼丽的笔墨,先构成一个美妙的梦境,把主人公放在特定的梦境欢会当中,使她在好梦惊醒以后,益增离别之苦,词意亦陡转沉郁。“惊残梦”以下转入正文,又用低徊咏叹的方式,先写门外是春光骀荡,而人“犹惊归”,于极度失望中,再展望归之情,词笔亦再作顿挫。换头处又以整妆期待的笔墨,使主人公凄清的内心世界,于纸上徘徊重现,不言其怀人而自见幽怨。词境由委婉转向深沉。结尾更从主人公的内心深处,迸发出“何处是辽阳?”的感慨,征人不归,他们的闺中少妇,却是在痴心等待。此妇所忆之人遭遇如何,不得而知。但一边是霜戈壁立、铁骑腾踏的边塞,一边是春意浓郁、锦屏寂寞的深闺,纵使重逢有望,也不知道在何年何月。因此“锦屏春昼长”一句,更深沉地揭示了主人公的怨思。咏叹至此,对主题发抒已达言有尽而意不尽的境界,在情节上也作出第三次的顿挫。不尽主人公在深思,也有“此恨绵绵”之感。
这是一首画面优美、引人入胜的小诗。它描绘了一幅生动的画面:一座幽静无人的园林,在蒙蒙丝雨的笼罩下,有露出水面的菱叶、铺满池中的浮萍,有穿叶弄花的鸣莺、花枝离披的蔷薇,还有双双相对的浴水鸳鸯。诗人把这些生机盎然、杂呈眼底的景物,加以剪裁,组合成诗,向读者展示了一幅清幽而妍丽的画图。诗的首句“菱透浮萍绿锦池”和末句“鸳鸯相对浴红衣”,描画的都是池面景,点明题中的“后池”。次句“夏莺千啭弄蔷薇”,描画的是岸边景。这是池面景的陪衬,而从这幅池塘夏色图的布局来看,又是必不可少的。至于第三句“尽日无人看微雨”,虽然淡淡写来,却是极为关键的一句,它为整幅画染上一层幽寂、迷朦的色彩。句中的“看”字,则暗暗托出观景之人。四句诗安排得错落有致,而又融会为一个整体,具有悦目赏心的美感。
这首诗之使人产生美感,还因为它的设色多彩而又协调。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指出“摛表五色,贵在时见”,并举“《雅》咏棠华,或黄或白,《骚》述秋兰,绿叶紫茎”为例。这首绝句在色彩的点染上,交错使用了明笔与暗笔。“绿锦池”、“浴红衣”,明点绿、红两色:“菱”、“浮萍”、“莺”、“蔷薇”,则通过物体暗示绿、黄两色。出水的菱叶和水面的浮萍都是翠绿色,夏莺的羽毛是嫩黄色,而初夏开放的蔷薇花也多半是黄色。就整个画面的配色来看,第一句在池面重叠覆盖上菱叶和浮萍,好似织成了一片绿锦。第二句则为这片绿锦绣上了黄鸟、黄花。不过,这样的色彩配合也许素净有余而明艳不足,因此,诗的末句特以鸳鸯的红衣为画面增添光泽,从而使画面更为醒目。
这首诗还运用了以动表静、以声响显示幽寂的手法。它所要表现的本是一个极其静寂的环境,但诗中不仅有禽鸟浴水、弄花的动景,而且还让蔷薇丛中传出一片莺声。这样写,并没有破坏环境的静寂,反而显得更静寂。这是因为,动与静、声与寂,看似相反,其实相成。王籍《入若耶溪》诗“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一句,正道破了这一奥秘。
这首诗通篇写景,但并不是一首单纯的写景诗,景中自有人在,自有情在。三、四两句是全篇关目。第三句不仅展示一个“尽日无人”的环境,而且隐然还有一位尽日看雨之人,其百无聊赖的情状是可以想见的。句中说“看微雨”,其实,丝雨纷纷,无可寓目,可寓目的应是菱叶、浮萍、池水、鸣莺、蔷薇。而其人最后心目所注却是池面鸳鸯的相对戏水。这对鸳鸯更映衬出看雨人的孤独必然使他见景生情,生发许多联想、遐想。可与这首诗参读的有焦循《秋江曲》:“早看鸳鸯飞,暮看鸳鸯宿。鸳鸯有时飞,鸳鸯有时宿。”两诗妙处都在不道破注视鸳鸯的人此时所想何事,所怀何情,而篇外之意却不言自见。对照两诗,杜牧的这首诗可能更空灵含蓄,更有若即若离之妙。
宝冠寺是雁荡山四大名刹之一。雁荡山以瀑布奇峰著名,这首诗打破常规,题目是题宝冠寺,重点不写雁荡的峰岩瀑布,甚至无一字写到寺庙,只是描绘环境的幽静,突出自己的心灵感受。
诗开门见山,首联就把自己置身在山寺中,写环境,抒感受。诗说自己漫步在寺内,在流水边驻足,凭倚着石栏杆,只觉得有一股说不出的清寒。清寒是人对外部气候的感受,没有什么难以表达之处,诗人说“不可云”,是因为山中寒冷,又逢岁暮,自然寒气逼人,这不是诗人唯一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如此幽寂的环境,使诗人心中产生了另一种清寒的感受,这感受很复杂,是淡泊名利、陶洗心境、出世达观等种种感受的总和,因此不可名状,难以叙述概括,只能用“不可云”三字来代表。虽然“不可云”,但必要抒发,诗接着便巧妙地借景达意,说眼见桥下流来清寒的泉水,想到其源头,抬头观望,岩洞谽然,由此便推测流水的清寒,是因为它是石洞中的云朵所化。这样写,境的清寒与人的高洁全都予以表露了。这种表现方法,就是历来诗家所说的“不写之写”,“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元好问《论诗》),不明白说,让读者自己品味。也达到了司空图《诗品》含蓄的标准:“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己,若不堪忧。是有真宰,与之沉浮……浅深聚散,万取一收。”
三、四联仍然用前两联手法,一联抒情,一联以景蕴情。环境如此岑寂,诗人的情怀如此淡泊,境与情吻合无间,诗人就不由自主地产生了留恋忘返的心情。第三联明白说出自己的情感,在表现时先抑后扬,出句说自己想在这里住段时间,可是正逢年末,非得回家去;因为不能住下的遗憾,对句便写自己在幽阒的环境中反复吟咏,不知不觉到了半夜。这样写,又回照了上文。尾联以景色来反衬心情的淡泊。雁荡山顶有湖,四季不干,是越冬大雁栖息的所在,雁荡山即以此得名。诗写听不见一声雁鸣,是实事,同时用以突出夜深时万籁俱静的场面。诗人在这样的深夜尚不回去,他的胸怀就自然可知了。
诗的第二联“流来桥下水,半是洞中云”是众口传颂的名联。诗人通过自己的感受,由水的寒想到高处的寒,由高处又想到云与水的关系,从而把两者相联系,表现那一特定环境与特定心情,赵师秀对云水之间常常产生通感,喜欢把它们组合成一个场景,或硬把它们相互联系,如他在另一首名作《薛氏瓜庐》中写道:“野水多于地,春山半是云。”诗这联,元方回《瀛奎律髓》曾指出是参考了唐杜荀鹤的“只应松上鹤,便是洞中人”句,这是从构思的角度上来说。如果从赵师秀喜在云与水上做文章的角度上看,诗更接近于武陵《赠王隐人》“飞来南浦水,半是华山云”句。赵师秀以苦吟出名,他曾经对人说:“一篇幸止有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未如之何矣。”(宋刘克庄《野谷集序》)他在写这联诗时,极有可能受到杜荀鹤、于武陵诗的启发。
赵师秀曾经选贾岛、姚合诗为《二妙集》,他的这首诗的风格即近似贾岛、姚合,诗面不用典故,写景造境简易平淡,结构严谨,意境清瘦,琢磨锻炼得不露痕迹。“永嘉四灵”的诗讲究雕镌后的归真,即纯用白描手法,绘景写情,虽然气格有些局促,但在当时江西诗派踔厉诗坛的情况下,无疑是给沉闷中注入了新鲜空气。赵师秀在“四灵”中成就最高,这首诗又是他的代表作,从此可以窥见“四灵”诗风的特点。
这首诗在写作手法上属于借题发挥,即借用石门长老的形象,抒发作者忠于朝庭、希望得到朝庭的理解和重新起用,而长期被冷落的悲愤失望的心情。
诗的首句通过“石门长老”的形象,引出作者往事如梦的感慨;第二句借“旃檀”的形象,说明官场新贵们的得势。三、四句再借“石门长老”之言,说明江山易主、改朝换代、作者的忠心无人理解,等待重新起用已经无望。五、六句以“石门长老”的形象和自白,慨叹人生易老和作者生平抱负的落空。“忘机”,就是已经“无意苦争春”。“贪爱都忘”,就是心的颓丧,不再有理想与追求。七、八句是诗的尾联,也是对全诗的总结。这两句通过对“东轩”外春日景色的描写,抒发了作者类似于“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感慨。作者以青春年少成名,并被委以朝廷重任,当年的意气风发可想而知。
“雉皆飞”含有一个典故,由乐府琴曲《雉朝飞》变化而来:“春秋时,卫侯女出嫁齐太子,中道闻太子死,傅母(女官名)仍然劝她去处理丧事。丧毕不肯归,终死于齐。傅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于冢上放之,忽二雉出墓中。傅母托雉曰:‘女果为雉也?’言未毕,雉俱飞而起,忽然不见。傅母悲痛,援琴作操,故曰《雉朝飞》。”也有人说:“《雉朝飞》为齐处士伤无妻之作。”柳宗元早年丧妻,来永州之后,母亲和女儿先后病逝,所承受的人生变故如同“屋漏偏遭连夜雨,行船又遇顶头风”,这种打击与悲痛可想而知。他被贬职后闲居永州,这期间江山易主,官场易人,新贵层出不穷,而且无不趋炎附势,对柳宗元等“俟罪”的闲官不屑一顾,或者颐指气使;更有一帮小人,经常散布一些流言蜚语,和莫须有的诬陷之辞。因此,诗人尽管悲愤交加,却不能在诗文中明明白白地流露出对朝廷的怨恨心情,只好运用巧妙的写作手法,通过“戏题”一诗,表面上是在劝戒石门长老,不要用老迈哀伤的心情,来观看东轩之外春意盎然的景色,以免触景生情,更加伤心;实际上是在劝慰自己,要忍辱负重,不与官场新贵们攀比,索性闭目塞听,让火热的心彻底地冷却,以免受到更大的伤害。
整首诗,以一个衰老、冰冷、绝望的外表,包容了一颗充满激情、火热和突突跳跃的心。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冰与炭的不可调和,最终决定了这位大才的悲剧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