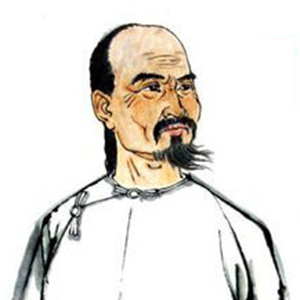这首诗的前两句勾勒出诗人拄着拐杖并顶着峭寒乘兴出游的形象,后两句中,诗人将自己的感情外化为原本无辜的秋风,出语诙谐,在豁达的情怀中透着浓重的悲秋情调。全诗语言通俗浅显而又耐人寻味,风格诙谐风趣而透着哀凉,在写作上不落俗套,自创新意,抒发了时光把人抛、人老见白头的愁绪。
“峭寒催换木棉裘,倚杖郊原作近游。”此诗开头一句就点出了深秋季节:时序更迭,秋气渐凛,料峭的霜风,阵阵中人,已使夹衣也难以御寒,必须换上木棉重裘了。枫叶红了的时候本不甚寒,正是“已凉天气未寒时”,但老人气血衰竭,已非此不可。江南深秋,棉袄也足可应付,但诗人已换上更为保暖的木棉重裘,可见其畏寒之极。其中,一个“催”字下得很有分量,言下有紧迫性,写出了光阴如箭,抛人无情的主观感受,实为三、四两句张本。接着的第二句通过几个短语,形象地刻画出主人公的龙钟老态,点出了题旨。“倚杖”并非“拖筇”,“近游”也非“远足”,脚力不济而只能就近盘桓散心的情形不言而喻。寥寥七字,把人物的情态和活动范围交待得十分清楚,一个在秋风中踽踽独行的伛偻老者的形象跃然纸上。与第一句共同勾勒出的形象是:在早寒的秋风中,诗人拄着拐杖,顶着峭寒,乘兴出游。在“峭寒”中,诗人的心情是旷达的、舒缓的,但难免有瑟索感。
“最是秋风管闲事,红他枫叶白人头。”由前两句的蓄势可知此处的怨悱绝非强说闲愁的调侃之词。秋风似一个守约的君子,年年如期而至,“管闲事”、煞风景”般地非要把枫叶吹红、青发染白不可,“红他枫叶”尚不足恨,因为第二年还可重发返青,“白人头”却是无从再黑了。本来秋风没有感情,也不好管闲事,枫叶之红、青丝之白,都与秋风没半点关系,诗人发此怪怨,实属无理。但越是无理,越是有情,诗人自入秋以来,一直不堪寒冷,再加上年事已高,感伤之情就从没断过,此刻他看到瑟瑟作响的红叶,一腔悲怀再也把持不住,便冲秋风抱怨道:“最是秋风管闲事。”这里的秋风,实际上已经超出它本身的含义,成为了整个秋天、甚至永远无情地流逝着的时间的代表,正是无情的岁月逼红了枫叶,也催老了诗人。在此,诗人将自己的感情外化为原本无辜的秋风,尽管仍不忘幽默,出语诙谐,色彩对比鲜明,又用与秋风对话的语气将秋风拟人化,说得轻松俏皮,显得活泼而特别有生气,流露出一种豁达的情怀,却也从中透出一种浓重的悲秋情调,蓄意悖理的手法让哀凉之感直达读者心灵深处,使人读而黯然。其中,末句采用“句中对”的形式。“红”与“白”的对照,使人感到衰飒之中犹不失清丽。此处,诗人将自己的感情外化为原本无辜的秋风,以蓄意悖理的手法,让哀凉之感直达读者心灵深处,仿佛读者自己已经成为了一个步履蹒跚的老者,在秋风中不禁洒泪。诗意或脱胎于蒋捷《一剪梅·舟过吴江》的“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但二者意境是有所不同的:蒋词写春景,伤春未免无聊;此诗写秋意,悲秋更觉沉挚。
全诗语言通俗浅显而又耐人寻味,风格诙谐风趣而透着哀凉,在写作上不落俗套,一扫“悲秋"、 “垂老叹”等传统作品低沉悲苦的调子,自创新意。
《劝学》中的“劝”起着统领全篇的作用。“劝”解释为“勉励”的意思。作者在这篇以《劝学》为题的诗歌中,劝勉青少年要珍惜少壮年华,勤奋学习,有所作为,否则,到老一事无成,后悔已晚。使孩子初步理解人生短暂,从而提高学习的积极性。诗歌以短短的28个字便揭示了这个深刻的道理,达到了催人奋进的效果。
“三更灯火五更鸡”是指勤劳的人、勤奋学习的学生在三更半夜时还在工作、学习,三更时灯还亮着,熄灯躺下稍稍歇息不久,五更的鸡就叫了,这些勤劳的人又得起床忙碌开了。第一句用客观现象写时间早,引出第二句学习要勤奋,要早起“正是男儿读书时”为第一句作补充,表达了年少学习时应该不分昼夜学习,通过努力学习才能报家报国,建功立业。
“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写的是年轻的时候不好好学习到了年纪大了,在想要学习也晚了。句子中“黑发”,“白首”是采用借代的修辞方法,借指青年和老年。通过对比的手法,突出读书学习要趁早,不要到了老了后悔了才去学习。从结构上看,三、四句为对偶句,“黑发”与“白首”前后呼应,互相映衬,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首诗深入浅出,自然流畅,富含哲理。核心是“黑发早勤学,白首读书迟”。作为有志气的人,要注意抓紧时间读书学习修身养性,最好的读书时间是在三更五更,晨读不息;而且只有年年月月刻苦坚持,才能真正学到报国兴家立业的本领。从学习的时间这一角度立意,劝勉年轻人不要虚度光阴,要及早努力学习,免得将来后悔。诗人是从学习的意义,作用和学习应持的态度方法等角度立意,希望人们重视后天学习,以加强自身的行为修养。
徐熥与其弟、藏书家“红雨楼”主人徐兴公,都是明朝后期闽中才子,徐兴公声名尤大,号“兴公诗派”。这首小诗,当是徐熥寄给正在客游途中的兄弟,望其早日归来聚首的。
前两句里,重叠着“春”“客”各三字,一时令人眼花缭乱,但细细读时,却只觉诗意层层迭变,全无重复之感。“春风送客”,佳事也,身在客途,有春风一路相送、殷勤追随、慰我寂怀,如何不佳?如何却是“翻愁客”?起句虽不设问,而疑问已在其中。次句答得更巧。“客路逢春”,其实与“春风送客”只是一事,但虽是一事,两样说之,滋味便全然不同。有春一路“送”我,固然良慰;但春者,当是于安闲悠然中所赏玩者也,今在“客路”,正尔奔波,有何闲逸心思赏玩呢?故客路所逢之春,在客子眼中,自然是“不当春”一一算不得春,彼虽欲慰我,却终不能慰我,彼既一路送来,却时时令我不得慰,又如何不愁?
上两句一问一答,已于重叠用字之中,曲尽变化之妙,但仅此而已,尚不过小巧手段,此诗之妙,更在后两句,然最妙处虽在后两句,其草蛇灰线,仍出于前两句。请再细想之:“不当春”,客因可作如是观,单春毕竟是春,不论你说它当得当不得,春风依旧骀荡,春光依旧汩汩流逝一一这,恐怕才是客愁的更深处吧?诗人唯因窥到了这客子在漫言“不当春”背后的深愁,故而于第三句才突发奇想,他把目光投到了象征春日的娇啭黄莺儿身上,他要那黄莹儿声音别变,还是嫩嫩的,娇娇的,千万别马上变得老腔老调,千万别把春天也啼老了,啼尽了一一因为,此际天涯正有一位未归的客子,正被算不得春的春光紧紧包裹着,为无法享有真正的、安闲的、故乡的春光而愁上加愁。如果黄莺儿声音真的老了、春光真的逝尽了,那客子天涯归来,他还能赏玩到什么呢?他岂不是要在“不当春”之外,更增一层“不见春”的悲哀?
诗中的“客”,当然是指徐兴公,诗人寄诗给乃弟,而不称“弟”称“客”,且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无非是为乃弟点醒客子身份,望他莫要久恋梁园,迷失故园。诗中言徐兴公“逢春不当春”,自是诗人的揣测;诗人要莺声不老、春光莫逝,自也是诗人的痴想。一篇之中,皆为揣测和痴想;一篇怀人盼归之文字,却皆为“愁客”、“未归”充满字面,诗旨并不显露;这般落笔是诗的出人意表处,是诗的不落旧套处,更是诗的尤可收取招人归来之效处。试想:若徐兴公看破了兄长的痴想,顿悟到莺声其实不得不老、春光其实不得不逝,他能不早作归计吗?他能让期望与故园的兄长,在春尽之际长吁短叹、失望独归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