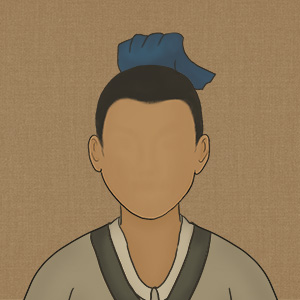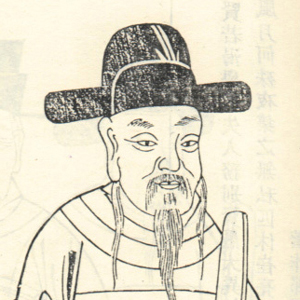梁启超的《读陆放翁集》作于他一八九九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出走日本期间,写的是读陆游诗集引起的感慨。这里所选的是其中一首。
诗的前两句从大处着笔,指出千百年来诗坛柔弱不振的总趋势。在这种柔媚纤弱的风气笼罩之下,那种刚健雄直的战斗性和勇于为国家献身的精神也消亡了。所谓「兵魂销尽国魂空」是「靡靡风」最突出的表现。作者格外强调这一点,乃在为下两句蓄势,抹倒「诗界千年」,正是为了突出一人。「集中十九从军乐」指诗题给出的《陆放翁集》。在「兵魂销尽国魂空」的「千年」诗界,唯有陆游的诗集里,十分之九都是抒写卫国从军的渴望和欢慰的。所以末句「亘古男儿一放翁」,使足笔力推崇陆游是从古至今的诗人中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诗末梁启超自注云:「中国诗家无不言从军苦者,惟放翁则慕为国殇,至老不衰」,将诗意说得就更明确了。全诗写得极为概括凝练,雄直警策,这些都表现为「诗界千年」同「一放翁」的艺术对比所显示出的鲜明性。
梁启超格外推崇爱国主义和为国而战的「尚武精神」,他认为「中国人无尚武精神」,表现在诗里,则所谓「诗界千年靡靡风」,因而他倡导「诗界革命」,欲改造文学,振作民气,达到救国拯民的目的。这首诗可说是其发自心声之作。
《菩萨蛮·萧萧几叶风兼雨》通篇用白描的写法,从多个方面去描写和渲染,写思妇的苦情。“风兼雨”“长更”是耳闻,“蟾蜍下早弦”是眼见,“夜寒”是身体感受,“无处不伤心”是心理感受。容若将离人苦夜长,相思难解,无处不伤心的苦况写得精细到位,末一句雅而伤,词中女子显然是淑女,风格姿态不同于《古诗十九首》里的“荡子妇”。“轻尘”两字更将闺阁寂寥的氛围摹写得深细。凄婉之情溢于词表。上片展现自然景象,秋天的风雨和秋天的月。下片是社会事相,泪花和灯花。
上阙写景。首句中,词人描写了凄风苦雨下,落叶萧萧的景象,渲染出一种悲凉的悲凉的氛围。“长更”一句,从李煜《三台令》词中化出,写长夜漫漫,无法入睡,词人索性抬头望天,不知不觉,月亮已在上弦处了,表明词人孤卧时间之久,寂寞难耐。词的下阙写词人好不容易入睡,却因凉夜被薄惊醒,孤凄寒冷透彻心扉,不觉泪水伴着灯花淌落。满心伤怀,更奈何,眼望去,竟是伊人昔日所弹之琴,如今古琴都蒙上了灰尘,更休提伊人如今飘然远去了。
词人所描之景,在古琴处停止,仿佛古琴余音,婉转低回,回味无穷。
韦司马,即韦爱。公元501年(齐东昏侯永元三年)春正月,萧衍为征东将军,从襄阳兴师讨伐东昏侯,留弟冠军将军萧伟行雍州(治所在今湖北襄阳)州府事,以壮武将军韦爱为其司马,带襄阳令。时齐兴太守颜僧都等据郡反,爱沉敏有谋,率众千余人,与僧都等战于始平郡南,大破之。公元502年(梁天监元年),进号辅国将军,寻除宁蜀太守,与益州刺史邓元起西上袭刘季连,行至公安,道病卒(见《梁书·韦爱传》)。此诗当作于公元501年韦爱为雍州司马时。
张玉谷说:“此送别后还家写意之诗,非送别时作也。”(《古诗赏析》)全诗三十句,可言为五个段落,每段六句。第一段写江边话别时难舍难言的情景。第二段写韦爱乘舟离去,作者登楼远望时的心情。第三段写送归路上的感受。第四段写到家所见情景。第五段写辗转思念、夜不成寐的苦况。可谓层次言明,结构谨严。
这首诗最突出的艺术特色之一,就是成功地运用了“顶真格”。所谓“顶真格”,就是以上句的末几字(词语或句子)做下句的开头,使语句递接紧凑而生动畅达,读来抑扬顿挫,缠绵不绝。亦称“联珠格”。这里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几乎句句“联珠”的,如李白的《白云歌送刘十六归山》:“楚山秦山皆白云,白云处处长随君。长随君,君入楚山里,云亦随君渡湘水。湘水上,女萝衣,白云堪卧君早归。”宋元时更流行为一种带游戏性的文体,如《中原音韵》载《越调·小桃红》:“断肠人寄断肠词,词写心间事,事到头来不由自,自寻思,思量往日真诚志,志诚是有,有情谁似,似俺那人儿。”一种是段与段之间“联珠”的,这首诗就是这样。全诗五段,每段最后几字与下段最前几字相同或稍有变化,如第二段结尾“汹汹浪隐舟”与第三段开头“隐舟邈已远”,第四段结尾“竹里见萤飞”与第五段“萤飞飞不息”,首尾两字完全相同;而第一段结尾“萧萧行帆举”与第二段开头“举帆越中流”,第三段结尾“知予衔泪返”与第四段开头“衔泪心依依”,首尾两三字则错综变化。运用“顶真格”,将全诗很自然地言为五个段落,每段都是六句,而且一段一换韵,平仄韵相间,又每段首句入韵。这样,从形式上看,非常整齐谨严,从声律上讲,读来反复顿挫,蝉联不断,大有缠绵悱恻,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妙,恰切地反映了主人公依恋难舍、思念不已的感情。所以沈德潜说:“每于顿挫处,蝉联而下,一往情深。”(《古诗源》卷十三)
另一个艺术特色,就是叠字的运用。全诗共用了六组叠字,都恰到好处。如“悯悯言手毕,萧萧行帆举”,将风催舟发主客不忍离别的情景维妙维肖地表现了出来。这或许是化用了梁简文帝萧纲《伤离新体诗》的“凄凄隐去棹,悯悯怆还途”诗意。“逦逦山蔽日,汹汹浪隐舟”,连绵起伏的山峦隐没了落日的光辉,也挡住了送行者的视线,友人乘坐的小船在惊涛骇浪中忽隐忽现,这既写出了旅途的艰险,又细微深刻地表现了作者对友人的担心和关切。离情别景,宛然在目。“依依”,思恋之貌,“暧暧”,昏昧之貌,而这“暧暧”的薄暮景象,与那“依依”的离情别绪交织在一起,更加增强了艺术的感染力量。
宫怨是唐诗中屡见的题材。薛逢的这首《宫词》,从望幸着笔,刻画了宫妃企望君王恩幸而不可得的怨恨心理,情致委婉,有其独特风格。
诗的首联,即点明人物身份和全诗主旨:“十二楼中尽晓妆,望仙楼上望君王。”“十二楼”、“望仙楼”皆指宫妃的住处。《史记·封禅书》记,方士言“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于执期”;又,《旧唐书·武宗本纪》记,“会昌五年作望仙楼于神策军”。诗中用“十二楼”、“望仙楼”代指宫妃的住所,非实指,是取其“候神”、“望仙”的涵义。这两句是说,宫妃们在宫楼之上,一大早就着意梳妆打扮,象盼望神仙降临一样企首翘望着君王的恩幸。
颔联通过对周围环境的渲染,烘托望幸之人内心的清冷、寂寞:“锁衔金兽连环冷,水滴铜龙昼漏长。”这两句说,宫门上那兽形门环被紧紧锁住,那龙纹漏壶水滴声声。上句“冷”字,既写出铜质门环之冰凉,又显出深宫紧闭之冷寂,映衬出宫妃心情的凄冷。下句“长”字,通过宫妃对漏壶中没完没了的滴水声的独特感受,刻画出她昼长难耐的孤寂无聊的心境。 颈联通过宫妃的着意装饰打扮,进一步刻画她百无聊赖的心理。“云髻罢梳还对镜,罗衣欲换更添香”,是说刚刚梳罢那浓密如云的发髻,又对着镜子端详,惟恐有什么不妥贴之处;想再换一件新艳的罗衣,又给它加熏一些香气。这一联将宫妃那盼望中叫人失望、失望中又怀着希望的心理状态,刻画得十分逼真。“望”的时间越长,越叫人心情难堪,说是没指望吧,又怀着某种期待;说是有希望吧,望眼欲穿,实在渺茫。罢梳复又对镜,换衣重又添香,不过是心情烦乱无聊和想望之极的写照。
末联写宫妃“望”极而怨的心情,不过这种怨恨表达得极其曲折隐晦:“遥窥正殿帘开处,袍袴宫人扫御床”。“袍袴”,指穿短袍绣袴的宫女。“遥窥”二字,表现了妃子复杂微妙的心理:我这尊贵的妃子成日价翘首空望,还倒不如那洒扫的宫女能接近皇帝!又表明,君王即将临幸正殿,不会再来的了。似乎有一种近乎绝望的哀怨隐隐地透露出来。
这首诗对人物心理状态的描写极其细腻、逼真。自首联总起望幸之意后,下三联即把这种“望”的心情融于对周围环境的描画、对人物动作的状写和对人物间的处境的反衬之中,生动地反映了宫妃们的空虚、寂寞、苦闷、伤怨的精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