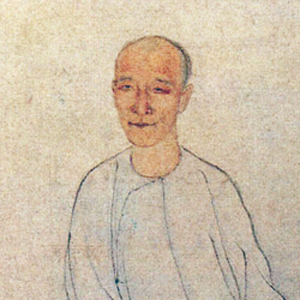“手风慵展一行书,眼暗休寻九局图。”中风,指四肢风痹。八行书,指信札。暗,是形容老眼昏花,视力不明。九局图,指棋谱。“手风”和“眼暗”,都写自己病废的身体。“慵展”和“休寻”,写自己索寞的情怀。信懒得写,意味着交游屏绝;棋不愿摸,意味着机心泯灭。寥寥十四个字,把那种贫病潦倒、无所事事的情味充分表达出来了,正点明诗题“安贫”。
“窗里日光飞野马,案头筠管长蒲卢。”就室内景物略加点染,进一步烘托“安贫”的题旨。野马,指浮游于空气中的埃尘,语出《庄子·逍遥游》。筠管,竹管,这里指毛笔筒。蒲卢,又名蜾蠃,一种细腰蜂,每产卵于小孔穴中。两句的意思是:闲居无聊,望着室内的埃尘在窗前日光下浮动,而案头毛笔由于长久搁置不用,笔筒里竟然孵化出了细腰蜂。这一联写景不仅刻画入微,而且与前面所说的“慵展”、“休寻”的懒散生活正相贴合,将诗人老病颓唐的心境展示得淋漓尽致。
“谋身拙为安蛇足,报国危曾捋虎须。”中“安蛇足”,即寓言“画蛇添足”,此处用以讽刺精心谋私。“捋虎须”,典出《庄子·盗跖》,孔子游说盗跖被驱逐后说:“丘所谓无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头,编虎须,几不免虎口哉!”比喻诗人忠于唐王室,敢于与权倾朝野的篡逆之臣进行抗争。如《新唐书》本传载:一次,权高震主的强藩朱温同崔撤“临陛宣事,坐者皆去席,握不动,曰:‘侍宴无辄立,二公将以我为知礼。’全忠(朱温)怒偓薄己,悻然出。”全联以表面上的谦逊之辞,叙述了诗人舍身为国的壮烈情怀。句中,前后两次用典,珠联璧合,情采熠然,丰厚的意蕴中,流动着刚直不阿的气势,突出地反映了诗人作为李唐王朝忠臣节士的形象。对此,元吴师道《吴礼部诗话》称之为“凛然有烈丈夫之气。”。
“举世可能无默识,未知谁拟试齐竽。”则又折回眼前空虚寂寥的处境。试齐竽,事见《韩非子·内储说上》:齐宣王爱听吹竽,要三百人合奏,有位不会吹的南郭处士也混在乐队里装装样子,骗取一份俸禄。后愍王继立,喜欢听人单独演奏,南郭处士只好逃之夭夭。这里引用来表示希望有人能像齐愍王听竽那样,将人才的贤愚臧否一一判别,合理使用。整个这一联是诗人在回顾自己报国无成的经历之后迸发出的一个质问:世界上怎会没有人将人才问题默记于心,可又有谁准备像齐愍王听竽那样认真地选拔人才以挽救国事呢?质问中似乎带有那么一点微茫的希望,而更多是无可奈何的感慨:世无识者,有志难骋,不甘于安贫自处,又将如何!满腔的愤懑终于化作一声叹息,情切而辞婉。
题作“安贫”,实质是不甘安贫,希望有所作为;但由于无可作为,又不能不归结为自甘安贫。贯串于诗人晚年生活中的这一基本思想矛盾以及由此引起的复杂心理变化,都在这首篇幅不长的诗里得到真切而生动的反映,显示了高度的艺术概括力。诗歌风貌上,外形颓放而内蕴苍劲,律对整切而用笔浑洒,也体现了诗人后期创作格调的日趋老成。前人评为“七纵八横,头头是道,最能动人心脾”(邵祖平《韩偓诗旨表微》),殆非虚誉。
这是郑晋外交斗争的一个回合。郑国处于晋楚两强之间,对于近邻的晋国要侍奉,可对于远一些的楚国也要朝拜,这还未计尚须在齐秦的周旋,察言观色仰人鼻息,夹缝中的苟活苦不堪言。但是晋国对此还很不满意。于是,郑国的执政大臣子家给晋国的执政大臣赵宣子写了这封信。这是一份照会,也可以说相当于一份最后通牒。在信中子家历数了郑君对晋的朝见,暗示其所表现出的恭顺已无以复加,如果晋再如此逼迫,不对现行政策改弦更张,那郑国只能是铤而走险,彻底投靠楚国,和晋国决一死战。文中只有三位人物:晋侯、晋国大臣赵宣子和郑国的执政子家。
郑国子家的照会,不是致意晋侯,而是“告赵宣子”,这因为赵宣子才实权在握,而他与晋侯,也有着十几年的、非同寻常的生死渊缘。
这个晋侯,是晋襄公的儿子夷皋,即晋灵公。晋文公流亡在外十九年,秦穆公送其渡河回晋已经有六十二岁了,他在位只有九年,就病死传位给太子姬欢,也即晋襄公。姬欢是晋文公逃亡前在蒲城的儿子,晋献公进攻蒲城时,文公逃亡,夷皋幸免于难,躲入民间。晋文公即位后他被文赢认为己子,估计其继位时候已经有四十多岁。有些学者认为,姬欢系文赢所生,很有些牵强,因为重耳从楚到秦才娶得文赢,且是当年就渡河复国,如姬欢为文赢之子,则继位时节不足十岁,哪里像秦晋崤之战时刚刚继位的晋襄公!何况晋襄公在位仅仅七年,却做成了不少大事,这绝非十三四岁的少年所能为。但是,也正是因为他避难民间,直至文公复国才来投奔,所以娶妻生子较晚,他死的时候太子夷皋还在襁褓。为了他继位的人选,晋国的大臣们很是争论了一番,他们觉得立夷皋为君,政局是不容易安定的,还不如立一位年长的公子。当时晋文公的从亡臣子,如赵衰、咎犯俱已亡故,执政的大臣是赵盾,就是本文所说的赵宣子,他是赵衰和叔隗之子,准备到秦国迎接晋襄公的弟弟公子雍,而贾季主张到陈国迎接公子乐。赵盾为此罢免了贾季官职,贾季逃亡翟国,赵盾派大将先蔑、重臣随会去秦国。
此时秦穆公亦故,秦康公继位。他认为必须以重兵送公子雍为妥。因为上次秦穆公送晋文公复国,还没有安定晋国国内的局势,就匆匆退兵了,结果吕甥、郤芮随即阴谋叛乱,若非勃鞮告密,还不知鹿死谁手。所以这次大军准备得很充分,随先蔑、随会缓缓而行。可是在晋国,此时却出现了变故:夷皋的母亲听说后,抱着太子上朝,把夷皋放在赵盾怀中:“先君在病重时,就把他的儿子交给你了,当时他嘱咐说,如果你能教诲他成才,那是对晋国的恩赐,如他不能成才,则就只能怨你失职。你为什么弃之另立?”诸位大臣哑口无言,只能是拥立夷皋继位,这就是晋灵公。赵盾自统大军,在令狐迎击秦军。秦康公是好心好意,帮人落得个冤家,先蔑随会也只好流亡秦国。赵盾扶保着一个孩子,晋国的内政外交是一手操持,所幸还有昆弟赵穿鼎力相助,十几年总算磕磕绊绊地走了过来。但是赵盾未得周公精神的精髓,周公旦辅佐周成王,是时刻不忘对侄子的教育;赵盾是位臣子,就不能太放肆,以避免流言蜚语,日久天长就培养出一位奢侈荒淫的君王,《史记》载:“十四年(新君继位时为元年)灵公壮,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观其避丸也。”何等的残暴!用弓弩发弹子伤人,观看无辜者逃跑躲避为乐;至于杀人更是家常便饭,一次杀了厨工,还让他的老婆背尸体去丢弃。赵盾多次劝谏,惹得晋灵公烦躁,曾几次派刺客去暗杀。赵盾不得已逃亡,还没有出境,赵穿就带兵袭杀了晋灵公迎赵盾回朝,晋国的民众对此都很拥戴。但是史官董狐仍然记录在案:“赵盾弑其君”,赵盾认为自己无罪,董狐指出赵为执政,逃亡还没有出境,返回后又不惩办赵穿,就应该负全责。后人评论认为,董狐记录实事求是,不为尊者隐匿过失;赵盾也是为了国家,确实是一位忠臣,背着黑锅有些可惜。事件后赵盾迎接公子黑臀(晋文公之子)立为晋成公。
郑国当时的国君是郑穆公,即郑文公之子子兰也。郑文公有三位夫人,但是她们所生的儿子都因罪死,文公一怒之下,将姬妾庶出的公子一律驱逐。公子兰逃奔晋国,侍奉晋文公谨慎,所以很得喜爱。晋文公出兵围郑时(见第一卷《烛之武退秦师》),秦穆公自行退兵,晋文公也只能和郑文公盟约,条件即是立子兰为太子。郑国的群臣认为,子兰在诸公子中最贤,立之对国家有利,于是子兰成了太子。两年后晋文公和郑文公相继而卒,子兰继位为郑穆公。子家是当时郑国的执政大臣,也是姬姓的公子,名归生。
本文涉及的史实发生在鲁文公十七年,即晋灵公继位的第十年,应该说那时他还是个青少年,国家事务的决断,仍须赵盾为之。子家致函赵盾,是相当适宜的,但是作为正式的外交照会,书面上仍然对着晋灵公。
晋灵公在詹会合诸侯,商议平定宋国内乱的事务,此间(于:在,是:这次)他没有会见郑文公,认为郑投靠楚国,对晋国已有 心。
——应该说明的是,詹就在郑国的地域,晋灵公在近边大会诸侯,却不召见郑文公,已经明显地表露出极大的不满。按照周朝在立国初对功臣、王室重要成员和前代君王后人的封爵,晋为侯爵而郑为伯爵,所以分别称其为晋侯郑伯。文中尚有蔡侯、陈侯亦然。——
郑国的执政大臣子家派执讯——即负责联络的官员——给晋国送来书信(与之:给晋君送来),以向赵宣子申述。
——子家的书信是给晋国的外交文书,本来其接受者是晋侯,但主持政务的是赵盾,子家也就不再绕弯子,总统还是个小孩子,我也不过是个代言人,那就直接和你这位总理交涉吧,但文书陈述的主要对象仍是晋侯。——
信中说:“我们国君继位才三年,就曾招蔡庄公(他也封爵为侯,故称蔡侯)来一同去侍奉贵国(当时是晋襄公),九月蔡侯到达以后(蔽邑:对自己地域的谦称)准备出发,但我国因为侯宣多事件——公子子兰逃亡晋国,在晋文公伐郑时,作为盟约条件被立为太子,当时一些郑国的大夫力促此事,其中包括侯宣多;两年后郑文公卒,侯又力保子兰继位为郑穆公,为此侯宣多居功专权,故子家称之‘侯宣多之难’——因此国君不能和蔡侯同往。十一月大体平定了侯宣多的作乱后,(在仅过了两个月之后)就紧随蔡侯去朝见襄公。十二年六月,我姬归生陪伴着太子夷,为陈国(陈侯:陈共公)要朝见晋须请命于楚国的事宜,专意来朝见君王禀告——这时候已经是晋灵公在位。十四年七月,我们国君又来朝见,从而促成(蒇:读chan,完成)了陈国的事情(作为楚国附属的陈来和晋和好),十五年五月,陈侯从我国出发前往贵国去朝见君王。去年正月,烛之武陪伴着太子夷又往朝见(往年:去年;往朝夷:应是‘夷往朝’,这是个倒装句,是因为在烛之武后面省略了‘佐’字)。八月我国君又亲去朝见。按说(以:释为按照)陈、蔡这样和楚亲近的国家(迩:读er,近,如遐迩闻名),却对晋不敢怀有 心,是(则:这里作判断词)我国的作用啊!虽然我们这样尽心地侍奉君王,为什么(何以)仍然不免获罪?我们国君继位以后,一次朝见襄公,两次朝见君王(这里的‘一’、‘再’指的是一次和两次,而不是‘首先’和 ‘然后’),太子夷和我国的几位大臣,相继到你们绛都朝拜。
——文中的这个‘孤’应该是郑穆公的自称,外交文书的言者其实就应该是国君,但本文是以子家的口气申述,例如自称‘归生’,称郑穆公为‘寡君’,称太子‘寡君之嫡夷’。可是这里却用‘夷和孤的二三臣’这种口气来称呼太子——直呼其名——和大臣们,只有郑穆公才有此资格。这可能是左丘明写书时有所失误。——
虽然我们是个小国,但尽心尽意地所做是没有(蔑:无)再能超越的了,现在大国(指晋)还说:‘你们没有满足(逞:使得逞)我的愿望’。那我们只有灭亡,因为确实已经再也无以复加了。古人说过:‘畏首畏尾,去了两头,身子还能剩下多少?’还说过:‘鹿在生死的关头,就顾不得选择庇荫的地方了(音:古通荫,即庇荫之处。这言外之意是,如果晋国逼迫得太紧,郑国也只能不得不投靠楚国了)。’小国侍奉大国,如能遇恩德相待,他们就是人;如不能被尊重,他们就是危机中的鹿,铤而走险——铤:快跑的样子,在险路上飞奔——急迫之中还有什么选择!你们的命令,已经超越了极限(罔极),我们知道就要亡国了,只能准备(将)悉数动员我军(赋:军队,因为那时是按照田赋出兵员的),开赴鯈地(鯈:读chou,在郑晋边界)迎候你们,现在只有听候您的决定了。文公二年我国也曾朝见齐国,四年,为齐国去攻击蔡国,结果是和楚国讲和(蔡国是楚的盟国)。居于大国之间而服从其强制性的命令,难道也是罪过吗?作为大国您要连这也不体谅,我们就已经不在乎违抗了。”
晋国于是派巩朔来郑国讲和、盟约,并把赵穿和晋君的女婿池(此人或许是晋襄公的女婿,因为晋灵公当时只十几岁)留在郑国作为人质。
这一篇照会,终使晋国赵盾审时度势,改变了对郑的外交策略。郑国在楚晋二强的夹缝中苟活,可以说对双方都毕恭毕敬,就如子家所说是无以复加了。而此时晋国仍不满意,也即要求专一敬我,这其实就断绝了郑国的生路。晋人不讲信义,曲沃翼都争锋,同族手足相残,借道伐虢而灭虞,对秦以怨报德,晋灵公的继位也是赵盾等出尔反尔的例证。如果郑国彻底和楚断绝来往,今日让赵盾心满意足,就必须面对楚国的讨伐。等到楚军压境,再向晋国求援是来不及的,只能死路一条。而晋又从不枉费钱粮,不像烛之武说秦退兵,穆公还留逢孙等驻守,反正屈从晋国是死,不从也就再无可加之刑了,郑虽军力绵薄,但也能拼死一搏,或楚国尚有体谅,倾力前来救援,绝路逢生也未可知,这才有了子家的呐喊。所谓哀兵必胜——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
子家的说辞,和展喜不同。虽然齐鲁和晋郑相互地位、关系有相似之处,但展喜是胸有成竹:当时的齐孝公内忧不断,伐鲁不过是炫耀武功,鲁国虽有灾荒,但人心同仇敌忾。齐军并不愿在疆场和鲁国对决,更不能粘着对恃。所以很顺利地说退齐兵。子家文书倒类似烛之武的方式,都是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都是在逻辑上引出第三方的砝码,让对方来权衡利弊,重新斟酌和我方的关系。所不同的是,子家的陈述面对的晋国,是威胁的主要发起方,而烛之武说秦穆公,面对是进攻联军的次要部分;因为当时晋文公是决心灭郑,没有改变的可能性——叔詹自杀都无济于事!但秦穆公的军事实力最强,具有左右局势的能量,而第三方砝码就是晋的图霸!所以谈判水到渠成。子家面对的晋灵公(也即赵盾),只有彻底折服郑国的愿望,却没有灭郑的力量——如果能够,他不必装模作样;郑国尚有一定的经济军事实力,不是陈蔡小国所能比,又地处中原战略要冲,是晋楚在争霸中最具价值的帮手。可以说,他们谁争取到郑国,就为称霸奠定了最有力的基础。子家的说辞,最让赵盾担忧的,不是“鹿死不择荫”,而是铤而走险——彻底地投靠楚国,甚至请楚派军驻守。这个砝码的重量,赵盾不可能不掂量。子家专门说到陈国,那么详尽地讲他先和陈侯去楚国请示,再和陈侯来晋国朝见。言外之意是:你看看楚国多大气,我们是不能只依靠你的!和解是最好,开战也可以,让我彻底背离楚国不可能!利弊得失您看着办吧。
全诗十六章,前八章每章八句,刺厉王失政,好利而暴虐,以致民不聊生,故激起民怨;后八章每章六句,责同僚,然亦道出厉王用人不当,用人不当亦厉王之过失。故毛传总言为刺厉王。
首章以桑为比,桑本茂密,荫蔽甚广,因摘采至尽而剥落稀疏。比喻百姓下民,受剥夺之深,不胜其苦,故诗人哀民困已深,呼天而诉曰:“瘼彼昊天,宁不我矜。”意谓:高明在上的苍天啊,怎么不给我百姓以怜悯呢!诗意严肃,为全诗之主旨。
次章至第四章,述祸乱之本,乃是缘于征役不息,民无安居之所。“四牡骙骙,旟旐有翩”,谓下民已苦于征役,故见王室之车马旌旗,而痛心疾首曰:“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具祸以烬。”意思是说:乱子不平息国家就要灭亡,现 在民间黑发的丁壮已少,好比受了火灾很多人都成为灰烬了。国以民为本,民瘼深重,而国危矣。诗人对此情况,更大声疾呼云:“於乎有哀,国步斯频!”感叹国运危蹙,必无长久之理,必致蹈危亡之祸。三章感叹民穷财尽,而天不助我,人民无处可以安身,不知往何处为好,因而引起君子的深思。君子本无欲无求,扪心自问没有争权夺利之心,但念及国家前途,不免发出谁实为此祸根,至今仍为民之病害的浩叹。四章感慨“我生不辰,逢天僤怒”。“我生不辰”,谓生不逢时。诗人之言如此,可见内心殷忧之深。他从人民的角度出发,痛感人民想安居,而从西到东,没有能安居的处所。人民怀念故土故居,而故土故居都因征役不息不能免于祸乱。人民既受多种灾难的侵袭,更担心外患侵凌,御侮极为迫切。天怒民怨,而国王不恤民瘼,不思改变国家的政治,因此诗人忧心如捣,为盼国王一悟而不可得深怀忧愤。仅此四章,已可见暴政害民,深重到何等程度。
五章至八章,是诗人申述为国之道,再进忠言。五章首二句“为谋为毖,乱况斯削”,是说谋虑周到,做事慎重,祸乱的情况就可以削减。继言“告尔忧恤,诲尔序爵”;是以老臣的口气,诫教国王:必须忧恤国事,慎于授官拜爵,选用贤能。解救国家之急难,有如解救炎热。解救炎热,要用凉水,好比解救国家危难,必须任用贤良。诗人用“谁能执热,逝不以濯”等语,谆谆告诫,陈述利害,可谓语重心长,譬喻也很确当。六章七章,从爱护人民的观点出发,表明百姓都很善良,他们勤于稼穑,以耕种养活“力民代食”的人(“力民代食”指官府役使人民劳动,取其收获养活自己)。因此官府要体恤民情,爱护人民,是为政的首要大事。六章“如彼遡风,亦孔之僾”,是说国王为政,不得人心,人民就如向着逆风,感到窒息丧气。人民虽有进取之心,但征役过重,剥夺过多,他们必然会产生难于效力之感。七章叙天降灾害,祸乱频仍,执政者只知聚敛,没有顾念人民认真救灾。由于为政昏乱,所以人民倍感痛苦。在诗中,诗人用人民的口气,警示国王,一则曰:人怨则天怒,天降丧乱,将灭我所立之王;再则曰:降此蟊贼之虫,庄稼都受到虫害而失收,天灾正是天之惩戒。下曰“哀恫中国,具赘卒荒”,则是感念人民受灾痛苦,连缀的土地,都受灾荒芜,而执政者昏乱,没有领导人民合力救灾,因而也不能感念上天减轻灾难。
诗的第八章再从用人的角度出发,言人君有顺理有不顺理,用人有当有不当。贤明的国君明于治道,顺情达理能认真考虑选用他的辅相。不顺理的君王,则与之相反自以为是,把小人当作善良,因此使得人民迷惑而致发狂。
以上八章是诗的前半,也是诗的主体,总说国家产生祸乱的原因,是由于厉王好货暴政,不恤民瘼,不能用贤,不知纳谏,以致民怨沸腾,而诗人有“谁生厉阶,至今为梗”之悲慨。
后八章责同僚之执政者,不以善道规范自己,缺乏远见,只知逢迎君王,加速了国家的危亡,更引起人民的怨恨。诗人感慨小人当权,也是厉王的过失,因而作成此诗,希望引起鉴戒。
第九章以“瞻彼中林,甡甡其鹿”两句起兴。鹿之为物,性喜群居,相亲相善。今同僚朋友,反而相谮,不能以善道相助,是不如中林之鹿。故诗人感慨“上无明君,下有恶俗”(朱熹《诗集传》)而有“进退维谷”之叹。
第十章、十一章,用对比手法,指责执政者缺乏远见,他们阿谀取容,自鸣得意,他们存有畏忌之心,能进言而不进言,反覆瞻顾,于是贤者避退,不肖者进,于是人民惨遭荼毒而造成变乱。诗人指出执政者倘为圣明之人,必能高瞻远瞩,明见百里,倘若执政者是愚人,他们目光短浅,倒行逆施,做了坏事,反而狂妄欣喜。这是祸乱之由。诗人又说:“维此良人,弗求弗迪。维彼忍心,是顾是复。”表明贤者不求名不争位,忍心之不肖者,则与之相反,多方钻营,唯名利是图;国事如斯而国王不察,亲小人,远贤人,于是百姓难忍荼毒,祸乱生矣。
第十二章、十三章以“大风有隧”起兴,先言大风之行,必有其隧;君子与小人之行也是各有其道。大风行于空谷之中,君子所行的是善道,小人不顺于理,则行于污垢之中。次言大风之行,既有其隧;贪人之行,亦必败其类。征之事实,无有或爽。盖厉王此时,用贪人荣夷公为政,荣公好专利,厉王悦之。芮良夫谏不听,反遭忌恨。故诗中有“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之语。可知厉王对于阿谀奉承他的话语,就听得进,进行对答,而听到忠谏之言就不予理睬。不用善良的人,反以进献忠言的人为狂悖,国家不能不危亡。
第十四章慨叹同僚朋友,专利敛财,虐民为政,不思翻然悔改,反而对尽忠的诗人进行威吓,所以诗人再作告诫。诗人说:“嗟尔朋友,予岂不知而作,如彼飞虫,时亦弋获。”意思是说:可叹你们这些同僚,我难道不知你们的所作所为?你们对国家有极大的危害,好比那些飞鸟,有时候也会被人捕获,国家动乱危亡,你们也不会有好的下场。诗人如此警诫,可渭声情俱历。可惜此辈小人,无动于衷,所以诗人在此章的结尾,以“既之阴女,反予来赫”作结,再次警告这些人说:我已熟悉你们的底细,你们对我也无所施其威吓了。
在第十五章中,诗人继第九至十四章指责执政臣僚诸种劣迹之后,更缕陈人民之所以激成暴乱的原因,实为执政者之咎,执政者贪利敛财,推行暴政,导致民怨沸腾,民无安居之所,痛苦无处诉说,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怨恨官府,走邪僻之路。此章诗云:“民之罔极,职凉善背。”指出人民之所以失去是非准则,是因为官府执政者推行苛政违背道理。“民之回遹,职竞用力”。指出人民之所以走向邪僻,是由于官府执政者尚力而不尚德。不仅如此,诗中还指出,执政者做对人民不利的事,唯恐不得其胜(意谓极其残酷)。谴责极为严正。诗人忧国之热忱,同情人民之深切,于此可见。《诗集传》所称此人此辈,即指助厉王为虐之荣夷公等,小人当权,加速国家之危亡,诚足引为鉴诫。
末章承前,言民之所以未得安定,是由于执政者以盗寇的手段,对他们进行掠夺,所以他们也不得不为盗为寇。上为盗寇之行,民心不能安定。诗人又以“凉曰不可,覆背善詈”两句,表示:我虽忠告你们,却又不被你们接受,反而在背后诅咒我。最后归结到作诗的缘由:“虽曰匪予,既作尔歌。”意谓:尽管你们诽谤我,我还是为你们作了这首歌,以促成你们的省悟。
此诗既叹百姓之困穷,又伤国事之昏乱;既探祸乱之根,又言救乱之道;既叹生不逢时,又伤救世无力;既指斥国君之昏庸,又斥群僚不敢进言;既斥责小人乱国之行,又指斥王之不能用贤。诗中显示出一种沉郁和忧伤的情调。
从诗的语言来看,全诗语言朴直而多变化,直陈己意,不事雕饰而寄意深长。其中许多用语,至今还被引用,还具有活力。如“瘼彼昊天,宁不我矜”,此呼天之词也。“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此忧时之词也。“谁生厉阶,至今为梗”,此愤世之词也。“谁能执热,逝不以濯”,此善譬之词也。“人亦有言,进退维谷”,此言处世之词也。古代语词,虽至西周,尚未发展到完美的程度,所以诗中多用通假字来满足表意的需要,有些词语,甚至解说纷纭,难有确意,但根据诗的主旨,仔细思考,还是可以顺理成章,得到合情合理的解说的,因为文字本是逐步发展起来的,从诗中可以看出诗人高度的操纵文字能力。
从表现手法来看,这首长诗,运用了比喻、反诘、衬托、夸张、对比等多种手法。
这首诗,着意刻画了作者贬官后的闲散之态和对隐居生活的向往。“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这两句说:游亭之后,便躺在纸屏遮挡的石枕、竹方床上,看了一会儿陶渊明的诗(“卧展柴桑处士诗”),感到有些倦怠,便随手抛书,美美地睡了一觉。诗人是“夏日登车盖亭”的,因而,读了“纸屏、石枕、方竹床”,写得气清意爽;读了“手倦抛书、午梦长”,表现了诗人闲散之态;并且从“午梦长”中,还透出一点半隐半露的消息,这要联系下文来理解。
“睡觉莞然成独笑”,梦醒之后,诗人“莞然独笑”,是在“午梦长”中有所妙悟,从而领略到人生如梦,富贵如云烟。。诗人所读的书,是“柴桑处士诗”;诗人所作的梦,也是耕樵处士之梦;梦中是处士,醒来是谪官,他想想昔为布衣平民(“持正年二十许岁时,家苦贫,衣服稍敝。”事见《懒真子》),鸿运一来,金榜题名,仕途廿载,官至丞相,后来天翻地覆,谪居此地,如同大梦一场。由此,他想到了归隐;想到归隐,马上便有隐者的呼唤——“数声渔笛在沧浪”。而听到了“数声渔笛”,他的归隐之情就表现得更加强烈了。
唐代诗人王维写过一首《酬张少府》:“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这首诗一方面明示作者“万事不关心”,一方面又描摹了他聆听“渔歌入浦深”的情状,所以归隐的题旨比较明显。而蔡确这首诗,却仅以“莞然独笑”、“数声渔笛”揭示主旨,这就比王维之诗更形委婉;更具韵外之致和味外之旨。《楚辞·渔父》:“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王逸《楚辞章句》注:“水清,喻世昭明,沐浴,升朝廷也;水浊,喻世昏暗,宜隐遁也。”描写闲散生活,委婉抒发归隐之志,便是这首诗的主旨。
上片先写天意留客。“秋风湖上萧萧雨,使君欲去还留住。”西湖上的晴雨变化是常见的现象,离任的太守陈襄将要远行,却被风雨留住。这是天从人意的美事,老天爷仿佛被送别的人们所感动,所以才特意以“萧萧雨”“留住”客人,满足了大家的心愿,这是老天有情。接下来苏轼笔锋陡然一转,“今日漫留君,明朝愁杀人。”为何这样写。接下去苏轼又把笔锋收回来,申述了一个使人信服的理由,“明朝愁杀人”原来是离情再经过一夜的酝酿和蓄积,会变得更深更浓,到明天送别时一下子爆发出来,会把人“愁”死的!可见老天有情,人更有情。经过这一纵一擒,心理上或情感上的回旋跌宕,苏轼将离情推向了纵深。
下片转换角度,写动人的送别场景。“留人千点泪,洒向长河水。”这两句写“留人”泣别,“留人”是指送别陈襄的一群官妓,同“长河水”联系起来,一方面是由于陈襄乘官船,从水程赴任,另一方面暗用了江淹《别赋》中的词语,“怨复怨兮远山曲,去复去兮长河水。” “留人”泣别是情重怨深的表现,这就把离情推向了一个高潮。“不用敛双蛾,路人啼更多。”这两句又峰回路转,别开境界。苏轼像是对“留人”们说,你们还是收住眼泪吧,且看站立在大路两旁的杭州百姓,他们哭得比你们还要伤心呢!广大百姓自愿前来送别一位离任的地方官,尽情挥洒泪水,离别场面庄严、感人。可以说,这是百姓对一位官员的最高褒奖。苏轼这样写,非溢美之辞。是苏轼从侧面写出了陈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政绩,在把离情推向极顶的同时,也暗含着对陈襄流惠于民的赞颂。
全词无一处直接抒写苏轼自己当前的离愁,苏轼仅仅是一个旁观者而已。但又无处不渗透了苏轼浓重的离情别绪。苏轼在对实际生活观察和体验的基础上,选取了独特的艺术视角,出奇制胜,使人感到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