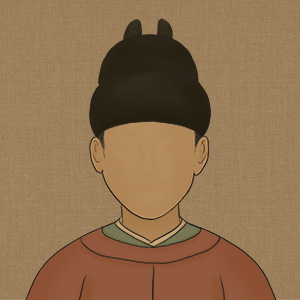据阮阅《诗话总龟》等书记载:“南唐卢绛病痁,梦白衣美女歌曰:‘玉京人去秋萧索’云云。”从此这首小词蒙上一层迷离恍惚的神秘色彩,被看作“鬼词”。其实,这只是一首倾诉闺情的篇章,它以笔致工巧,深婉动人,赢得了人们的喜爱,曾在北宋初年广为流传。从词中可知,抒情主人公是一位温柔多情、敏感娴静的女子。
“玉京人去秋萧索,画檐鹊起梧桐落。”在这萧索的秋天,心上的人儿远去京城,庭院画檐下喜鹊飞起,梧桐纷纷飘落。
玉京,本道教所谓天上宫阙,用作京城的代称。在一个秋日的黄昏,她凭栏凝视,沉浸在对远方亲人的怀念之中。起首两句描绘出一幅飒飒秋景,景中有情。前一句点出秋气而“人去”之意,是情与景双双写入之法。“萧索”二字是一篇眼目,后一句就此点染。喜鹊历来是吉祥之鸟,鹊起而不顾,暗示丈夫一去杳无音信,闺中的主人公怅然失望也已隐然可见,细微如梧桐落叶之声清晰可闻,庭院之阒寂,女子怀想之深也可以想见了。“人去”,令人记起往昔未去之时;“萧索”,烘衬出抒情者的悲凉意绪,连带说出便觉情景相生,这正是双入法的妙处,由此开篇,全词都笼罩着瑟瑟寒意了。基调也由此确定。
“攲枕悄无言,月和清梦圆。”这两句是说,倚靠着枕儿默然远想,月儿和梦境都是那么的圆美。
接下来时间由黄昏而入夜。如果说前面两句侧重渲染气氛的话,那么这两句着重刻画人物的动作。中心落在思念二字上。夜不安寐,倚枕无言,用动作表现心理,形象而又委曲。“无言”是静默之状,又含“脉脉此情谁诉”之意。唯其默然远想,才引出下一句的清梦来。不知过了多久,这位辗转反侧的女子渐渐进入梦乡。梦中见到了她久别的亲人。词人把这梦中团聚和中天月圆巧妙的交织在一句之中,“圆”字双关。梦境沐浴着月的清辉,而一轮圆月又在梦的幻影之中,境界惝恍迷离,清幽怡人。梦境与现实,月色与人事两相对照反衬,使主人公的情怀表现得愈婉愈深了。
“背灯唯暗泣,甚处砧声急。”这两句是倒装句,说,不知什么地方响起阵阵捣衣声,把她从睡梦中惊醒,眼前的冷寂,益发加深了感伤和怅惘,她怎能不柔肠寸断,哀泣不止呢?
“甚处”,说明砧声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是一种并不太响,而且时断时续的声音,也符合乍醒来时恍惚莫辨的情态。这种声响竟把人惊醒,可知夜之静谧了。这样看来,句中极醒目的“急”字恐怕侧重于表现人的内心感受,未必是实写砧声。“背灯暗泣”乃梦断神伤之状。“暗”字兼言情、景,思妇心境之黯然具体可感。从上文的“攲枕悄无言”到此刻的“背灯暗泣”,层层叠进,愈转愈悲了。
“眉黛远山攒,芭蕉生暮寒。”结末两句是说,室内女子黛色如远山的眉头紧攒,室外圆月清辉之下芭蕉也觉瑟瑟寒意。
给那攒蹙的秀眉一个特写镜头,把满怀的思念和哀怨全部凝聚在黛色如远山的眉间了。末句轻轻宕开,以景收束:“芭蕉生暮寒”。凄冷之意有真切,又朦胧,那寒气直沁入人的心里,却又不曾说破。词婉而情切,令人哀感无端,正是所谓已经结情的妙笔。
这首词在结构上,一句景,一句情,间或情景双写。在情与景的相映、相生、相融之中,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婉曲而深切的袒露出来了。
这首诗开篇以钟山龙蟠、石头虎踞的地形之固胜引入至对历史的追思和感慨。借“钟山龙蟠,石城虎踞”的典故道出金陵城的帝王气象,而长江更成天堑,为王朝抵挡住了北方政权的入侵,偏安于江左的六朝人饮酒作乐,咏歌寻欢。但李白并非旨在写六朝的辉煌,颈联中的“空”字透露出了衰亡气息。“四十余帝三百秋,功名事迹随东流”,盖言金陵为帝都历史已久,王琦注《金陵歌送别范宣》中指出“自孙权定都建业(金陵),传四主”,晋元帝南渡时,金陵已是历时五十九年的“旧长安”,随后又经宋、齐、梁、陈四朝,帝王大业共传三百三十余年。接着思维的触角又伸向侯景破丹阳之童谣传说,从而引出对往昔的追念“金陵昔时何壮哉,席卷英豪天下来”,接续而后又转写豪华落尽的悲凉,进一步抒发面对历史的沧桑之感。
“冠盖散为烟雾尽,金舆玉座成寒灰”这一句之内的时空跨越与今昔对比令人心惊而顿感悲凉,诗歌的情感基调由先前的气势雄大转为怀古悼今、感时伤物的伤感凄凉。扣剑悲吟空咄嗟,梁陈白骨乱如麻。天子龙沉景阳井,谁歌玉树后庭花。历史的风云变幻、战争的离乱凄惨、朝代的更迭替代都委婉深沉地寓于其中。这首歌行体送别诗开篇描写石头钟山的形胜,将大半部分用于追述与金陵一地有关的重要历史事件。直到篇末才道出送别之意。“送尔长江万里心,他年来访商山皓。”在一篇之内将写物、怀古、咏史、送人、抒情都囊括其中。
全诗整体上,前四句主要是以触景生情为主,描绘钟山龙蟠、石头虎踞的雄奇壮观,生动地画出了一幅大自然的神奇壮丽图,妙笔生辉,令人心旌摇荡。接着八句诗词借“钟山龙蟠,石城虎踞”的典故道出金陵城的帝王气象,抒写六朝豪华落尽的悲凉,委婉深沉,沧桑之感油然而生,今昔对比,尽显顿感悲凉。最后八句诗词描绘朝代更迭替代、战争离乱之凄惨,六朝人饮酒作乐,咏歌寻欢,再也一去不复回。
全诗熔写物、抒情、怀古、咏史、送人为一体,对历史兴衰的感怀,所含挣扎幽愤多,既有个人仕途不得志、怀才不遇之意,亦有对家国渐渐衰亡而忧虑,诗词创作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主要表现为侧重抒写豪迈气概和激昂情怀,一旦感情兴发,就毫无节制的奔涌而出,常有异乎寻常的衔接,随情思流动而变化万端。
李贺流传后世的二百多首诗中,“鬼”诗有十多首。此诗写秋天来临时诗人的愁苦情怀,从其阴森料峭、鬼魅飘飘的风格来看,就是一首“鬼”诗。
“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这原是古往今来有才智之士的共同感慨。诗人对于时光的流逝表现了特异的敏感,以致秋风吹落梧桐树叶子的声音也使他惊心动魄,无限悲苦。这时,残灯照壁,又听得墙脚边络纬哀鸣;那鸣声,在诗人听来仿佛是在织着寒天的布,提醒人们秋深天寒,快到岁末了。诗开头一、二句点出“秋来”,抒发由此而引出的由“惊”转“苦”的感受,首句“惊心”说明诗人心里震动的强烈。第二句“啼寒素”,这个寒字,既指岁寒,更指听络纬啼声时的心寒。在感情上直承上句的“惊”与“苦”。
这一、二两句是全诗的引子。一个“苦”字给全诗定下了基调,笼罩以下六句。“谁看青简一编书,不啼花虫粉空蠹”,上句正面提问,下句反面补足。面对衰灯,耳听秋声,诗人感慨万端,他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自己写下的这些呕心沥血的诗篇,又有谁来赏识而不致让蠹虫白白地蛀蚀成粉末呢?”情调感伤,与首句的“苦”字相呼应。
五、六句紧接上面两句的意思。诗人辗转反侧,彻夜无眠,深深为世无知音、英雄无主的忧愤愁思所缠绕折磨,似乎九曲回肠都要拉成直的了。诗人痛苦地思索着,思索着,在衰灯明灭之中,仿佛看到赏识他的知音就在眼前,在洒窗冷雨的淅沥声中,一位古代诗人的“香魂”前来吊问他这个“书客”来了。这两句,诗人的心情极其沉痛,用笔又极其诡谲多姿。习惯上以“肠回”、“肠断”表示悲痛欲绝的感情,李贺却自铸新词,采用“肠直”的说法,愁思萦绕心头,把纡曲百结的心肠牵直,形象地写出了诗人愁思的深重、强烈,可见他用语的新奇。凭吊这种事情,一般只是生者对死者做,他却反过来说鬼魂前来凭吊他这个不幸的生者,更是石破天惊的诗中奇笔。
“雨冷香魂吊书客”,诗人画出了一幅十分凄清幽冷的画面,而且有画外音,在风雨淋涔之中,他仿佛隐隐约约听到秋坟中的鬼魂,在唱着鲍照当年抒发“长恨”的诗,他的遗恨就像苌弘的碧血那样永远难以消释。诗人表面上是说鲍照,实际上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胸中的块垒。志士才人怀才不遇,这正是千古同恨的事情。
此诗上半篇采用的是常见的由景入情的写法,下半篇则是全诗最有光彩的部分。“思牵今夜肠应直”,在牵肠情思的引发下,一个又一个恍惚迷离的幻象在眼前频频浮现,创造出了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以幻象写真情的独特境界。诗人深广的悲愤与瑰丽奇特的艺术形象之间达到了极其和谐的统一。在用韵上,后半篇也与前半篇不同。前半篇虽然悲苦、哀怨,但还能长歌当哭,痛痛快快地唱出,因而所选用的韵字正好是声调悠长、切合抒写哀怨之情的去声字“素”与“蠹”。到后半篇,与抒写伤痛已极的感情相适应,韵脚也由哀怨、悠长的去声字变为抑郁短促的入声字“客”与“碧”。
这是一首著名的“鬼”诗,其实,诗所要表现的并不是“鬼”,而是抒情诗人的自我形象。香魂来吊、鬼唱鲍诗、恨血化碧等等形象出现,主要是为了表现诗人抑郁未伸的情怀。诗人在人世间找不到知音,只能在阴冥世界寻求同调,感情十分悲凉。
“紫箫吹散”活用弄玉与萧史的传说,劈头就写出夫妇的离散,也暗示原先的恩爱。“燕子”“空楼”用唐代张尚书后,姬人关盼盼怀念旧爱,居张氏第中燕子楼十余年而不嫁的故事,进一步说明自己同李氏间生死不渝的爱情一“空”字,尤能令人联想到苏轼《永遇乐》词“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的名句。紧接着连用三种象征:明月已缺,难以再圆;玉簪中断,无由再续;覆水入地,无法重收,喻说事情的无可挽回。自古视花好月圆为美满的象征,此时词人的内心世界中已是“璧月长亏”。“玉簪”句用白居易《井底引银瓶》诗:“井底引银瓶,银瓶欲上丝绳绝;石上磨玉簪,玉簪欲从中央折。瓶沉簪折知奈何,似妾今朝与君别。”诗里用“覆水”传说的如骆宾王《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情知覆水也难收”,又李白《妾薄命》:“雨落不上天,覆水难再收”。
诸作皆言弃妇事。以下接着写从书信中了解到李氏的心情。霞、雾一类辞,是唐宋诗词描写道家生活的常见语。殷勤的青鸟,捎来了李氏的信。以“碧云句”,即江淹诗“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拟休上人怨别诗》)。她诉说幽闭在道观里的凄寂难堪。虽作了女道士,可情缘难断,缠绵悱恻之辞,正似苏蕙织的回文锦字,又好比唐代宫女的红叶题诗,饱含多少幽怨;但现实无情,已是仙凡异路了。
下片写在悠悠隔绝的痛苦中,转而追怀往日恩爱。
记得彼此初见是在谷口园林的客栈,银屏掩映,低声笑语。而此时回想起来,仿佛是场美好的梦。情景冉冉如昨,醒来却是一片新愁。词情至此,低徊无已。紧接着忽然掀起高潮。词人说,难道此生就这样永远不能看见了吗?不,他要拿分收的半镜,去寻找出高价出售的人,也许有重圆的一日。这结笔二句,仍是用前一首“鸾鉴分收”的故事。不过,前面是取其破镜之意,这里却是用其重圆之义。徐德言与乐昌公主夫妻诀别,各执半镜,约她日后以正月望日卖镜于都市,冀可相见。后来果真被他言中。(见唐孟棨《本事诗·情感》)“皇州”即京都,原是故事里卖镜的地方,活用不必拘泥。两词原是一组,前说被镜之痛,后说重圆之愿。破镜重圆之一典故的反复再见,并非雷同的运用,而标志着词中悲剧历程的起点与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