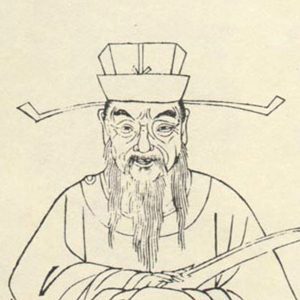《燕燕》全诗四章,前三章重章渲染惜别情境,后一章深情回忆被送者的美德。抒情深婉而语意沉痛,写人传神而敬意顿生。
前三章开首以飞燕起兴:“燕燕于飞,差池其羽”,“颉之颃之”,“下上其音”。《朱子语类》赞曰:“譬如画工一般,直是写得他精神出。”阳春三月,群燕飞翔,蹁跹上下,呢喃鸣唱。然而,诗人用意不只是描绘一幅“春燕试飞图”。而是以燕燕双飞的自由欢畅,来反衬同胞别离的愁苦哀伤。此所谓“譬如画工”又“写出精神”。接着点明事由:“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父亲已去世,妹妹又要远嫁,同胞手足今日分离,此情此境,依依难别。“远于将之”、“远送于南”,相送一程又一程,更见离情别绪之黯然。然而,千里相送,总有一别。远嫁的妹妹终于遽然而去,深情的兄长仍依依难舍。这里诗歌运用艺术手法表现出感人的情境:“瞻望弗及,泣涕如雨”,“伫立以泣”、“实劳我心”。先是登高瞻望,虽车马不见,却行尘时起;后是瞻望弗及,唯伫立以泣,伤心思念。真是兄妹情深,依依惜别,缠绵悱恻,鬼神可泣。这三章重章复唱,既易辞申意,又循序渐进,且乐景与哀情相反衬;从而把送别情境和惜别气氛,表现得深婉沉痛,不忍卒读。
四章由虚而实,转写被送者。原来二妹非同一般,她思虑切实而深长,性情温和而恭顺,为人谨慎又善良,正是自己治国安邦的好帮手。她执手临别,还不忘赠言勉励:莫忘先王的嘱托,成为百姓的好国君。这一章写人,体现了上古先民对女性美德的极高评价。在写法上,先概括描述,再写人物语言;静中有动,形象鲜活。而四章在全篇的结构上也有讲究,前三章虚笔渲染惜别气氛,后一章实笔刻画被送对象,采用了同《召南·采蘋》相似的倒装之法。
《燕燕》之后,“瞻望弗及”和“伫立以泣”成了表现惜别情境的原型意象,反复出现在历代送别诗中。“伫立以泣”的“泪”,成为别离主题赖以生发的艺术意象之一。
这首《蕃女怨》写来并不见一点“蕃”味,仍是一般的思妇词。这首词写飞燕双双还巢,引发了思妇的离愁别恨。女子在杏花(香雪)开放的日子里,于细雨中看到旧时双燕又嬉戏于梁间,于是想到她远征在边塞的丈夫。
“万枝香雪开已遍,细雨双燕”,写一个春天已经来临,浓郁的春意,自然反衬出思妇的寂寞。“钿蝉筝,金雀扇,画梁相见”意在突出女主人公的青春美丽,加强怀念之情。思妇正当难耐寂寞,一会儿拨弄着镶嵌着金蝉的筝,一会儿把玩着画着金雀的扇子的时候,旧日的燕子双双飞回到画梁上的旧巢。思妇为此受到极大的触动,于是发出深深的慨叹:“雁门消息不归来,又飞回。”这对燕子去年还在梁上的时候女主人公就盼着丈夫回家,此时燕子去了又飞回,而征人一点消息都没有。如此,词中的杏花闹春与空闺寂守,燕燕双飞与人影独立,燕子还巢与人不归家等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思妇之怨也就是从这几重对比中体现出来的。
在温词中,此首属于较为浅直的作品,辞藻不算艳丽,含义也还显豁。但是仍具有某些深曲之作的特点:只客观地提供精美的物象情态,而隐去它们之间的表面联系,留下大片想象余地。像“钿蝉筝”、“金雀扇”、“画梁相见”三者之间就省略了许多话,而这些物象情态的关系,很容易领悟出来,所以反而显得浅而不露,短而味永。
这首词上片写途中所见所闻,起写春色无边,点明时令,次写人们以极大的热情拥向南山觅春;下片紧承上片,继写沿途所见,并在结尾表达了自己的美好心愿,揭出作意。此词情由景出,论随情至,写得自然、得体。
正月的时候正值孟春,初阳发动,故词以“无边春色”起头。但是,就人之常情来说,尽管到处是春色,还是要去寻春、觅春的。次句的“苦”字表达出了人们这种寻觅春色的执着。词中的“南山”,大约指的是春光优美之处,也是作者邀请提刑官应懋之游春的目的地。“村村”三句,以及下片“翁前”两句,写的是农村“人日”这一天的热闹景象,是作者“觅”春所见,这也正是此词写作的一个重点。作者先大笔挥洒,用“箫鼓”、“笛”写节日歌舞之盛,用“村村”、“家家”极写范围包容之大,仅此一句,就将农村“人日”的风俗景象以及人们的欢乐情绪形象地渲染出来。“祈麦祈蚕”,点出“村村箫鼓家家笛”这项活动的目的。祈求农事丰收,这里虽举“麦”、“蚕”为诸多农事的代表,但在“人日”来说,农民马上可以接触到的一般来说,也就是麦与蚕了。这时,麦田泛出青绿之色,蚕在春天的气息里孵化,富于生机。对丰收的盼望与担忧,都同时在农民心头慢慢升起,他们要用这尽情的箫鼓和笛声表达他们心中的祈求。“来趁元正七”,这句是上片的结语,明确指出了特定时期季节性的内涵。
下片“翁前”两句,转入具体的描绘。“翁前子后孙扶掖”,这正是“来趁元正七”的老老少少,子子孙孙。魏了翁是南宋著名理学家,他对长幼之序极为重视,这从“翁”、“子”、“孙”的排列顺序中可以看出来。“商行贾坐农耕织”,这一组活动,由商、贾、农三种行当的人物组成,而作者用“行”、“坐”、“耕织”三个词,点明了三种行当人物的特征,语言简练。在古代,商人们分为行商和坐商两种。“耕织”则为“农”的本业。当然,这里不一定实写“人日”所见,而是作者由人们的祈求而联想到的各种自食其力的人所从事的争取丰收、幸福的实践活动。但这三个动词,却描绘出了一片繁忙景象。从“箫鼓”至“耕织”,这五句从不同的角度描绘出了农村的欢乐景象,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作者将种种苦闷、烦忧,都排斥在画面之外了。这里简直是一片桃源乐土。在偏安的半壁河山之中毕竟还有这样一片乐土!但其中也不排斥寓含着作者的理想,这正是他所苦苦寻觅的“春色”,上片次句用“苦”与“觅”两个字,用意就在于此。词的末三句,是作者就此情此境所引发的感想,是此词的哲理所在,也正是作者的希望。“须知”是告诫语,作者要告诉人们:“人日”中的“人”的种种活动与期望,古往今来,概莫能外,“人”是向上的,都在追求着幸福与美好;但是,人们如果都懂得做人的道理,都象在“人日”里所意识到“人”的作用与追求,那就“日日是人日”了,也就不会只有在“人日”这一天才去追求祈祷了。显然,作者是在勉励人们追求不息生生不止。这也正是作者思想核心之一。他处理政务主张“内修”、“立本”、“厚伦”,正人心,化风俗;他所留驻的州县,皆“以化善俗为治”;使“上下同心一德,而后平居有所补益,缓急有所倚仗”(均见《宋史》本传),这就是他在此词中发挥议论的思想基础。
从全词看,此词没有浮躁怪诞之气,写得古朴自然,平易真切,与农村风物极相贴合。
这首诗的主题,旧说大体相同,《毛诗序》说:“《谷风》,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绝焉。”朱熹也认为是朋友相怨之诗,但他没有将伤友道之绝与刺周幽王硬拉到一起。方玉润《诗经原始》认同朱熹的观点,并力驳《毛诗序》“刺幽王”之说穿凿空泛。今人高亨的《诗经今注》、程俊英的《诗经译注》等均取弃妇之诗说。陈子展《诗经直解》虽仍取旧说,但又说:“此诗风格绝类《国风》,盖以合乐入于《小雅》。《邶风·谷风》,弃妇之词。或疑《小雅·谷风》亦为弃妇之词。母题同,内容往往同,此歌谣常例。《后汉·阴皇后纪》,光武诏书云:‘吾微贱之时,娶于阴氏。因将兵征伐,遂各别离。幸得安全,俱脱虎口。……“将恐将惧,维予与女。将安将乐,女转弃予。”风人之戒,可不慎乎!’此可证此诗早在后汉之初,已有人视为弃妇之词矣。”
诗中的女主人公被丈夫遗弃,她满腔幽怨地回忆旧日家境贫困时,她辛勤操劳,帮助丈夫克服困难,丈夫对她也体贴疼爱;但后来生活安定富裕了,丈夫就变了心,忘恩负义地将她一脚踢开。因此她唱出这首诗谴责那只可共患难,不能同安乐的负心丈夫。
诗歌用风雨起兴,这手法同《邶风·谷风》如出一辙,两首《谷风》诗的主题也完全相同,这大概是在风雨交加的时候最容易触发人们的凄苦之情。被丈夫遗弃的妇女,面对凄风苦雨,更会增添无穷的伤怀愁绪,发出“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哀叹。
此诗语言凄恻而又委婉,只是娓娓地叙述被遗弃前后的事实,不加谴责骂詈的词句,而责备的意思已充分表露,所谓“怨而不怒”,说明主人公是一位性格善良懦弱的劳动妇女。这也反映了几千年以前,妇女就处在被压迫的屈辱境地,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