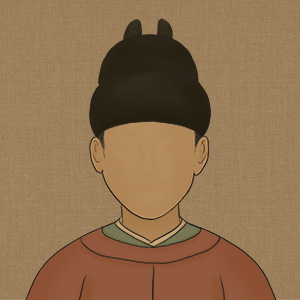和凝的《江城子》共有五首,是一组完整的组词,内容相连,叙述一位女子与情人夜间约会相见的整个过程,从第一首“排红烛,待潘郎”到第五首“天已明”,写出这位女子含娇、含恨、含笑、含情、含愁的一个等待恋人时特有的心态流程,表现出她对恋人的一片痴情。因为它“章法清晰”,所以被人誉为“联章之祖”,又称“江城五支,为言情者之祖”。所谓“江城五支,为言情者之祖”,指的应该并不是“托美人以写情,指落花而自喻”,而应该是采用组词这种特别的方式,叙述了一件完整的情事过程。这属于和凝的首创,所以称祖。
《江城子·迎得郎来入绣闱》为第四首,写女子与情人相会情景,两情相悦的情状描摹得十分生动。
鬓云松令,原名苏幕遮, 唐教坊曲名。双调六十二字,前后段各七句、四仄韵。范仲淹有一首著名的《苏幕遮·怀旧》“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含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后周邦彦《苏幕遮》词中有“鬓云松,眉叶聚。一阕离歌,不为行人驻”之句而得名鬓云松令。纳兰性德写过两首鬓云松令, 本篇咏浴是其一。
美人出浴是现代影视作品、西方美术中的常见题材。然而在我国的浩瀚的诗歌中却不多见,词里面有以此来形容花的,如李清照的“香脸半开娇旖旎,当庭际,玉人浴出新妆洗”,却极少有直接以此作为主题的来吟咏的,仅见过有五代阎选的《谒金门·美人浴》,清代 徐石麒的《南乡子 美人浴》和纳兰的此篇。
本词的上半阙写美人入浴。
“鬓云松,红玉莹” 写入浴前美人散开的乌发和晶莹的肌肤。以玉石喻女子之肌肤,如东坡《诉衷情·琵琶女》词“肤莹玉,鬓梳蝉,绮窗前”。 “早月多情,送过梨花影“ 写时令,暮春梨花季节,新月初升时分,同时暗写月下女子洁白的浴衣或身躯。”半饷斜钗慵未整,晕入轻潮,刚爱微风醒“ 。写她慵懒的泡在水中,半晌没有动静,腾腾的热气烘得她泛起了红晕。或许头也有点晕了,刚好一阵微风吹来,吹醒了她,好舒服啊!
词的下半阙写美人出浴。
“露华清,人语静”。夜幕降临,起露了,外面安静下来。美人出浴了,身上带着的水滴就像那晶莹的露珠。外面突然的安静,反而让她有点担心会不会有人偷窥刚出浴的她。”怕被郎窥,移却青鸾镜“,殊不知,移镜这个小动作,还有她的轻盈的步履都被郎看在眼里呢!不光看在眼里,而且为她担心,只穿了单衣的她能不能耐得住这星星出来之前的夜寒呢。“罗袜凌波波不定,小扇单衣,可耐星前冷”?罗袜凌波典出曹植的《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形容女子步履轻盈,像走在水面上,荡起细细的涟漪。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发端二句飘然而至,虽明白如话,但决非一览无味,须细加玩味。词人连用梨花、杏花比拟,可知所咏之物为花。道是梨花——却不是,道是杏花——也不是,则此花乍一看去,极易被误认为梨花,又极易被误认为杏花。仔细一看,却并非梨花,也并非杏花。因此可知此花之色,有如梨花之白,又有如杏花之红。
“白白与红红”紧承发端二句,点明此花之为红、白二色。连下两组状色的叠字,极简炼、极传神地写出繁花似锦、二色并妍的风采,也暗指它风韵别具一格,既有梨花之白,又有杏花之红,白中带红,如佳人冰雪肌肤微露红晕,有娇羞之态。 “白白”、“红红”两组叠字,简练、传神,使人如亲眼目睹红粉交错、繁花满枝的娇妍景致。
“别是东风情味”上句才略从正面点明花色,此句词笔却又轻灵地宕开,不再从正面著笔,而从唱叹之音赞美此花之风韵独具一格,超拔于春天众芳之上。实在少此一笔不得。可是,这究竟是一种什么花呢?
“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结笔仍是空际著笔,不过,虽未直接点出花名,却已作了不管之答。“曾记。曾记”,二语甚妙,不但引起读者的注意,呼唤起读者的记忆,且暗将词境推远。“人在武陵微醉”,武陵二字,暗示出此花之名。陶渊明《桃花源记》云:武陵渔人曾“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华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终于来到世外桃源。原来,此花属桃源之花,花名就是桃花。句中“醉”之一字,写出此花之为人所迷恋的感受。词境以桃花源结穴,馀味颇为深长。它可能意味着女词人的身份(宋词习以桃溪、桃源指妓女居处),也可能有取于桃花源凌越世俗之意。
此词所咏为红白桃花,这是桃花的一种,“桃品甚多……其花有红、紫、白、千叶、二色之殊。”(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果部》)红白桃花,就是同树花分二色的桃花。北宋邵雍有《二色桃》诗:“施朱施粉色俱好,倾城倾国艳不同。疑是蕊宫双姊妹,一时携手嫁东风。”诗虽不及严蕊此词含蕴,但可借作为此词的一个极好注脚。
此词绝不同于一般滞于物象的咏物词,它纯然从空际著笔,空灵荡漾,不即不离,写出红白桃花之高标逸韵,境界愈推愈高远,令人玩味无极而神为之一旺。就艺术而言,可以说是词中之逸品。
一至八句述舟行风涛之险.杜甫在岳阳受到当地朋友热情款待,在一个春水泛滥红日高照的时刻,躬腰告辞主人,乘着帆船,沿湘江南行。从岳阳到长沙是逆水行舟,朱崖澄澈,江涛汹涌,又遇恶风,可以想见,舟行极不顺利。诗人没有用夸张手法正面描写,“舟楫风涛之险”,却着力描写船夫、仆役废寝忘餐地与风浪搏斗,战胜艰险的经过。
九至二十句描写沿途所见官府横征暴敛迫使人民家破人亡的悲惨情景。浦起龙说:“中十二句,从‘采蕨’寡妇触发出来,随以‘闻见略同’句,推广畅论,极淋漓恺恻之致。”作者见到沿江山石间采蕨的妇女,因无钱缴纳苛捐杂税,只得把采来的野菜送到市场出售,用卖得的钱向官府交税。而她的丈夫此时已被繁重徭役折磨致死,她疲惫不堪,回到人烟稀少的村子,触景生情,号啕不止。诗人由亲眼见到令人摧肝折胆的悲惨景象,而联想平日听见与此大略相同的事例,同情之心由然生起。很显然,出现在诗人笔下的是具普遍意义的典型。 “贵人”们视人民如“莠蒿”,他们残酷剥削人民,不放过“锥刀之末”的微利。他们和爪牙“黠吏徒”巧立名目,勒索,掠夺百姓财物,造成千家逃亡,嗷嗷告谁。他从一个侧面深刻地揭露了残酷的社会现实,反映了人民的痛苦,表现了热爱人民的精神。
最后两句带有总结性质。诗人说,此次乘舟远涉,历尽风涛之险,固然劳苦极了,但同繁重徭役赋税压迫下的人民相比,自己总还能生活下去。尽管暮春三月百花盛开的时节还穿着旧棉袄,但也感到心“甘”情愿。这当然是诗人无可奈何聊以自慰的话。一个曾经在朝廷任职的大诗人,在春暖花开季节尚无春衣更换,那么广大穷苦百姓当时生活的困苦就可想而知了。这两句也反映了杜甫把个人生活置之度外,始终关心着广大人民的痛苦的博大胸怀。
此诗是杜甫晚年之作,但从中可以看出,他精神不减当年,对黑暗社会现实进行深刻揭露和辛辣讽刺,依旧放射出现实主义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