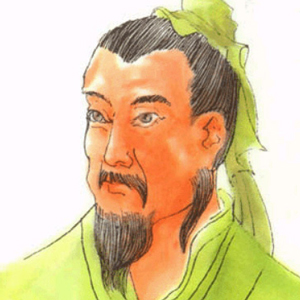第一首以20世纪30年代文化战线上“围剿”和反“围剿”这一充满刀光血影的尖锐斗争场景为背景,反衬出鲁迅先生坚定的意志和无畏的气概。称颂鲁迅先生在阴森恐怖的环境里,毫无畏惧地以笔作刀枪,与敌人鏖战。
第二首从精神文化渊源上发掘鲁迅先生与他家乡历史上爱国诗人陆游、秋瑾一脉相承的关系,赞颂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使鲁迅精神得以升华。
《七绝二首》第一首的起句盛赞鲁迅的广阔襟怀,远见卓识,以及坚如磐石的原则立场。大气包举,笼罩全篇。次句承转。“刀光剑影”一词形象地再现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之后白色恐怖的严酷。“任翔旋”生动描写了鲁迅在文化“围剿”下英勇无畏、机动灵活的战斗英姿。鲁迅后期娴熟地掌握了辩证法,不但高瞻远瞩,爱憎分明,而且巧妙地运用了“钻网战术”、“壕堑战术”,使一时其势汹汹的文氓、文探、文化刽子手们终于一败涂地。鲁迅在反文化“围剿”战役中建树的不朽功勋,鲁迅后期杂文所取得的辉煌思想艺术成就,都是辩证法的胜利。第三句宕开一层,具体点出了轰动中外文坛的左联五烈士遇难事件,内容由虚而实。“龙华喋血”,系指国民党政府于1931年2月7日秘密杀害二十余位革命志士(其中包括左联五烈士)的骇人听闻的暴行。现已查明,这批革命者是在集会抵制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上推行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时而分头被捕的。左联五烈士的牺牲,使鲁迅经历了继三一八惨案、四一二政变之后的又一次巨大震动。他因自己失去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去了很好的青年而彻夜不眠。先前,鲁迅阅读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神曲》一书的“地狱篇”,曾惊异于这作者设想的残酷,但目睹革命者淤积的凝血,鲁迅感到但丁还是仁厚的:“他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在已极平常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
末句统摄全诗。一个“犹”字,突出了鲁迅在黑暗暴力的进袭面前不避风险,挺然屹立,顽强抗争的韧的战斗精神。“小诗”,指鲁迅的《七律·惯于长夜过春时》(亦称《无题》或《悼柔石诗》)。这首诗慷慨悲怆,气壮情真,表达了鲁迅“怒向刀丛觅小诗”的坚强斗志。毛泽东爱读鲁迅诗,尤欣赏鲁迅那些激情澎湃、笔挟风雷的诗句,并常予援引,用以教育党内外同志。毛泽东显然对鲁迅的这首千古绝唱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并把这首诗视为体现鲁迅革命精神的代表作之一。
《七绝二首》第二首虽然字面上未提鲁迅,但却深刻揭示了鲁迅赖以植根、成长的文化沃土和给鲁迅以丰富精神滋养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与第一首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七绝之二的首句,寓情于景,由物及人,景、情、人融为一体。“鉴湖”“越台”是鲁迅故乡浙江绍兴的代表性景物,象征着萌生于于越部族时代的源远流长的吴越文化。“名士”一词在这里泛指在中国历史上为国家进步、民族振兴作出过不同贡献的仁人志士。鲁迅在《〈会稽郡故书杂集〉序》中写道:“会稽古称沃衍,珍宝所聚,海岳精液,善生俊异”,意思与此相同。在绍兴辈出的“名士”中,鲁迅就是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七绝之二次句的“忧忡”,即忧心忡忡,形容绍兴历代先贤具有为国为民忧虑不安并舍身相报的美德。“痛断肠”,形容这些优秀人物在国运艰难、危机四伏的年代痛心疾首,力挽狂澜于既倒。从“壮心未与年俱老,死去犹能作鬼雄”的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到临刑前以“秋风秋雨愁煞人”为唯一供词的反清志士、鉴湖女侠秋瑾,就都具有一脉相承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激情。他们的优秀诗作,连同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年代制作的小诗,无一例外地成为了中国诗歌宝库的珍品,全都融入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血脉。
毛泽东《七绝二首》遣词造句都是从内容出发,随意挥写,有的诗句并不完全为格律所拘。全诗风格雄浑,气势挺拔,充满阳刚之美。诗中的议论与形象相结合,与史实相结合,运用了一些并不生僻的典故,增强了作品的概括力,激起了读者的无尽联想。毛泽东这两首七绝的成功,既取决于他对古典诗词的深厚造诣,又取决于他对鲁迅作品和精神的深刻理解。他虽然运用的是旧体诗的形式,但描写的是新的人物,渗透的是新的感情,闪耀着的是时代精神的光芒。鲁迅《七绝·赠人二首》中有“须臾响急冰弦绝,但见奔星劲有声”之句。毛泽东《七绝二首》中诗句,音量之宏,音力之厚。
1937年,当鲁迅逝世一周年之际,在延安举办了纪念会,毛泽东发表了专门的演说,深入地论述了鲁迅的精神,称赞了鲁迅的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后来毛泽东多次提到鲁迅。
1961年9月25日,是鲁迅诞辰八十周年纪念日。为了纪念鲁迅,毛泽东写下了这首诗。
第一首以20世纪30年代文化战线上“围剿”和反“围剿”这一充满刀光血影的尖锐斗争场景为背景,反衬出鲁迅先生坚定的意志和无畏的气概。称颂鲁迅先生在阴森恐怖的环境里,毫无畏惧地以笔作刀枪,与敌人鏖战。
第二首从精神文化渊源上发掘鲁迅先生与他家乡历史上爱国诗人陆游、秋瑾一脉相承的关系,赞颂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使鲁迅精神得以升华。
《七绝二首》第一首的起句盛赞鲁迅的广阔襟怀,远见卓识,以及坚如磐石的原则立场。大气包举,笼罩全篇。次句承转。“刀光剑影”一词形象地再现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之后白色恐怖的严酷。“任翔旋”生动描写了鲁迅在文化“围剿”下英勇无畏、机动灵活的战斗英姿。鲁迅后期娴熟地掌握了辩证法,不但高瞻远瞩,爱憎分明,而且巧妙地运用了“钻网战术”、“壕堑战术”,使一时其势汹汹的文氓、文探、文化刽子手们终于一败涂地。鲁迅在反文化“围剿”战役中建树的不朽功勋,鲁迅后期杂文所取得的辉煌思想艺术成就,都是辩证法的胜利。第三句宕开一层,具体点出了轰动中外文坛的左联五烈士遇难事件,内容由虚而实。“龙华喋血”,系指国民党政府于1931年2月7日秘密杀害二十余位革命志士(其中包括左联五烈士)的骇人听闻的暴行。现已查明,这批革命者是在集会抵制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上推行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时而分头被捕的。左联五烈士的牺牲,使鲁迅经历了继三一八惨案、四一二政变之后的又一次巨大震动。他因自己失去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去了很好的青年而彻夜不眠。先前,鲁迅阅读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神曲》一书的“地狱篇”,曾惊异于这作者设想的残酷,但目睹革命者淤积的凝血,鲁迅感到但丁还是仁厚的:“他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在已极平常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
末句统摄全诗。一个“犹”字,突出了鲁迅在黑暗暴力的进袭面前不避风险,挺然屹立,顽强抗争的韧的战斗精神。“小诗”,指鲁迅的《七律·惯于长夜过春时》(亦称《无题》或《悼柔石诗》)。这首诗慷慨悲怆,气壮情真,表达了鲁迅“怒向刀丛觅小诗”的坚强斗志。毛泽东爱读鲁迅诗,尤欣赏鲁迅那些激情澎湃、笔挟风雷的诗句,并常予援引,用以教育党内外同志。毛泽东显然对鲁迅的这首千古绝唱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并把这首诗视为体现鲁迅革命精神的代表作之一。
《七绝二首》第二首虽然字面上未提鲁迅,但却深刻揭示了鲁迅赖以植根、成长的文化沃土和给鲁迅以丰富精神滋养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与第一首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七绝之二的首句,寓情于景,由物及人,景、情、人融为一体。“鉴湖”“越台”是鲁迅故乡浙江绍兴的代表性景物,象征着萌生于于越部族时代的源远流长的吴越文化。“名士”一词在这里泛指在中国历史上为国家进步、民族振兴作出过不同贡献的仁人志士。鲁迅在《〈会稽郡故书杂集〉序》中写道:“会稽古称沃衍,珍宝所聚,海岳精液,善生俊异”,意思与此相同。在绍兴辈出的“名士”中,鲁迅就是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七绝之二次句的“忧忡”,即忧心忡忡,形容绍兴历代先贤具有为国为民忧虑不安并舍身相报的美德。“痛断肠”,形容这些优秀人物在国运艰难、危机四伏的年代痛心疾首,力挽狂澜于既倒。从“壮心未与年俱老,死去犹能作鬼雄”的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到临刑前以“秋风秋雨愁煞人”为唯一供词的反清志士、鉴湖女侠秋瑾,就都具有一脉相承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激情。他们的优秀诗作,连同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年代制作的小诗,无一例外地成为了中国诗歌宝库的珍品,全都融入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血脉。
毛泽东《七绝二首》遣词造句都是从内容出发,随意挥写,有的诗句并不完全为格律所拘。全诗风格雄浑,气势挺拔,充满阳刚之美。诗中的议论与形象相结合,与史实相结合,运用了一些并不生僻的典故,增强了作品的概括力,激起了读者的无尽联想。毛泽东这两首七绝的成功,既取决于他对古典诗词的深厚造诣,又取决于他对鲁迅作品和精神的深刻理解。他虽然运用的是旧体诗的形式,但描写的是新的人物,渗透的是新的感情,闪耀着的是时代精神的光芒。鲁迅《七绝·赠人二首》中有“须臾响急冰弦绝,但见奔星劲有声”之句。毛泽东《七绝二首》中诗句,音量之宏,音力之厚。
文章从秦晋相好说起,历数秦穆公、康公、桓公时代,两国由交好到引发争端的种种情况,表明晋国在“肴之师”、“令狐之役”、“河曲之战”、“辅氏之聚”等双方争端中每次都是因秦怎么样,我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切入正题,说明这次“令狐会盟”秦的失约和不是,但狄、楚都已通报,晋国早有准备,是战是和由秦君定夺。这是一篇完整的外交辞令,结构严整,句法变化错综,行文步步紧逼,不容辩驳,虽然言语中真假搀杂甚至强词夺理,但深意曲笔,文字铮铮,开战国纵横家游说之辞和后世论辩书信的先河。
文章第一段对秦恩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在秦晋两国关系史上,也曾有过友好的时代,正所谓“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将女儿伯姬(穆姬)嫁给秦穆公。公元前637年,晋文公重耳逃亡秦国,秦穆公嫁以女儿怀羸。所以后世以男女通婚谓之结秦晋之好,献公宠骊姬,杀太子申生,“文公如齐,惠公如秦”。重耳逃亡各国十九年,最后一站是秦国,夷吾先后逃亡梁国和秦国。晋惠公夷吾和晋文公重耳两兄弟都是在秦国的鼎力相助下才得以回国登上君位的,秦对晋实有再造之恩。吕相却将此说成是“穆公不忘旧德,俾我惠公能奉祀于晋”,指穆公虽然做了好事,但那只是报答晋国的旧德而已。紧接着又指责秦国“而为韩之师”,好事做得不彻底,所以“不能成大勋”。公元前645年秦晋韩原之战的原因是晋惠公为得君位曾许秦五座城,回国后却又食言;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输粟于晋,输粟船队自雍及绛相继,人称“泛舟之役”。第二年,秦国发生饥荒,晋国却不卖给秦国粮食。韩原之战,晋惠公被俘,交割了原先答应的五座城,又以太子为人质,才回到晋国。作为战争双方来说,实在是晋国理屈,有负秦恩,但在吕相绝交书中,倒好像战争的责任在秦国似的。所以下文秦穆公“亦悔厥于心”,支持晋文公顺利登上君位。吕相绝秦书中只有这一段涉及了历史上两国存在友好关系,但吕相绝不是为秦歌功颂德来的,而是为战争即将爆发来递交绝交书,所以他把秦国友好行为说成是“不忘旧德”,“悔于厥心”,可谓深文曲笔,煞费苦心。
文章第三段对秦罪浓墨重彩,极力渲染,吕相对两国历史上的友好关系轻描淡写,但对秦国的“罪咎”却是不吝笔墨。在绝秦书中,秦国韩原之战是第一罪;公元前630年秦晋共同攻打郑国,秦穆公在郑大夫烛之武的游说下,和郑国私下订盟撤军回国,是第二罪;公元前627年,晋文公去世,秦穆公不来凭吊,反而侵犯晋国肴地,灭掉与晋同姓的滑国,妄图倾覆晋国,是第三罪;公元前626年,秦国因为肴之战战败,释放楚国俘虏,约定秦楚合作反对晋国,幸而上天有灵,楚太子商臣弑楚成王,秦国的阴谋才没有得逞,这是第四罪;公元前620年,秦康公即位,秦帅师送公子雍回国即位,被晋军在令狐击败,是第五罪;公元前615年,秦军为令狐之役伐晋,取晋羁马,两军战于河曲,是第六罪;秦桓公即位后,公元前594年,秦国利用晋国进兵伐赤狄灭潞国的机会,侵入晋国靠近黄河的州县,焚烧晋国的箕、郜两地,抢割庄稼、屠杀边境人民,秦晋因此有辅氏之战,这是第七罪。在历数了秦国的罪状之后,吕相才切入令狐会盟的正题,声讨秦国背盟的不义。在指斥秦国背盟时,吕相先用白狄告我,再用楚人告我,引告我。是秦反复无常的罪证。尤其是引楚王所述秦国之语:“尔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既暴露了秦国见利忘义的嘴脸,又刻画了秦国两面三刀的作法,使秦国无所逃其咎。令狐背盟是秦国言而无信、背信弃义、唯利是图的代表作,故吕相抓住不放,大作文章。
文章第四段在论述秦康公、晋灵公时期两国关系恶化时,绝秦书先点明“康公我之自出”,康公母亲是晋献公女儿,本是至亲,但他“又欲阙剪我公室”,“摇荡我边疆”,简直是六亲不认,实在不像话。“我是有以令狐之役”,又是被迫采取的行动。可“康犹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剪我羁马。”这等于说,给他改过的机会,他犹不思改悔,反而变本加厉。所以“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是康公绝我好也。”事实是,晋襄公死后,晋大夫赵盾等因太子夷皋年幼,都主张立公子雍。于是派先蔑、士会等到秦国去迎接公子雍,秦国亦派兵护送。可是晋襄公的夫人穆羸出来反对,坚持要立太子夷皋。赵盾临时变卦,改立夷皋,即晋灵公。赵盾派兵拒秦,在令狐把秦兵击退。后公子雍就客死秦国。本来是晋国前去迎公子雍,却说成是秦“帅我蟊贼”,有意颠覆晋国,真理都在晋国,责任全在秦国,讲理能讲到这种地步,吕相的口才实在令人惊叹。
吕相这篇绝交书,历数秦穆、康、桓三王和晋献、惠、文、襄、景五君之事,上溯源流,下及当世,行文纵横捭阖,笔力阳刚雄健,给后世以很大影响。其后秦作《讥楚文》,即仿效此书。吕相绝秦书开战国策士游说之辞先河,也是后世檄文之祖。
《春赋》是一支明快的春之圆舞曲,又是一幅绚丽的春之游乐图。描写了统治阶级春游时的狂欢极乐,曲折地表现了梁初社会繁荣气象,表现了一种得意的升平的欢乐情绪。全赋以大量的典故与轻靡的情思来表现对春天的赞美,辞藻绚丽,对仗工整,充分表现了六朝的绮靡文风。
此赋曲折地表现了梁初社会繁荣气象,表现了一种得意的升平的欢乐情绪。当然,在这篇赋中是找不到人民的艺术形象的。它所描写的是统治者和宫妃们在“春苑”中的欢乐情景和热闹场面。但衡量作品,并不能因为描写的对象是统治者和宫妃,就否定它有反映现实的价值。作品的客观效果往往是大于作家的写作意图的。只要把它和作者《哀江南赋》的“于时朝野欢娱”一段并读,就能体会到它很艺术地表现了梁初社会的太平景象了。
这篇《春赋》篇幅虽小,却通篇都是对偶,称之为他的前期代表作,从文学上看也是当之无愧的。庾信不仅在赋和诗中经常使用对偶,就是在碑文中也是习惯于用对偶的。对偶对庾信来说是语言习惯,是常用的语言模式,成了他的语言风格的一部分。《春赋》是由三十一个对偶组成的。从头到尾无一不是对偶。其中只有一联,在形式上可以不算对偶。“三日曲水向河津,日晚河边多解神”其实这也可以算做宽式对偶,是明显对称的。同时,此赋大量运用修辞手法,包括比喻、夸张、比拟、映衬等,用典尤其多,共有十一个典故。其中开头十二句就用了八个典故。
“赋”的本义是敷陈其事。作为文体,则是要“铺采摘文,体物写志”(《文心雕龙·诠赋》)。庾信的这篇赋偏于写景,耽于逸乐,夸饰宫廷生活,无非为帝王的游赏助兴,其志趣无可称道。所可称道者,在于铺采摘文的手段,选声炼色的造诣。就造句形式上说,开头与结尾处多七言句,声律近于诗,正所谓启唐人七古之先鞭。末段五、七言句相杂成文,婉转流利,风情翘秀。至于“眉将柳而争绿,面共桃而竞红”二句,不但属对精绝,而且刻画微妙。后来,初唐的王勃效仿庾信的《马射赋》中“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一句,在《滕王阁序》中造句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堪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再就描摹声色上说,《春赋》亦不乏秀句。如“钗朵多而讶重,髻鬟高而畏风”,下笔轻灵,形象宛在;“影来池里,花落衫中”,自然流出,却有无尽情致。又如“月入歌扇,花承节鼓”,读之如见其形,如闻其声,令人心醉目眩。庾信的早年赋作多事白描,此赋亦然。但是,白描中溢光流彩,绮靡宕逸,这正是庾信远俗独到之处。
这首《浣溪沙》词是苏轼43岁在徐州任太守时所作。公元1078年(元丰元年)春天,徐州发生了严重旱灾,作为地方官的苏轼曾率众到城东二十里的石潭求雨。得雨后,他又与百姓同赴石潭谢雨。苏轼在赴徐门石潭谢雨路上写成组词《浣溪沙》,共五首,这是第四首。作品描述他乡间的见闻和感受。艺术上颇具匠心,词中从农村习见的典型事物入手,意趣盎然地表现了淳厚的乡村风味。清新朴实,明白如话,生动真切,栩栩传神,是此词的显著特色。此词上片写景,下片抒情。需要指出的是,这首词中所写的景,并不是一般情况下通过视觉形象构成的统一的画面,而是通过传入耳鼓的各种不同的音响在诗人意识的屏幕上折射出的一组联续不断的影象。
这首词是苏轼在徐州(在今江苏省)作官的时候写的。按照当时的迷信风俗,一个关心农事的地方官,天大旱,要向“龙王爷”求雨;下了雨,又要向“龙王爷”谢雨。这首词就是苏轼有一次途经农村去谢雨,记下的见闻之一。
“簌簌衣巾落枣花”,按照文意本来应该是“枣花簌簌落衣巾”。古人写诗词,常常根据格律和修辞的需要,把句子成分的次序加以调动,这里就是如此。“簌簌”,是形容枣花纷纷落下的样子。“衣巾”,是衣服和头巾。古代服装,男人往往戴头巾。枣树在初夏开出黄绿色的小花。作者不是从旁边看到落枣花,而是行经枣树下,或是伫立枣树下,这样枣花才能落到衣巾上。接下去,“村南村北响缫车”。“缫[sāo]车”,一种抽取蚕丝的手摇工具。村子里从南头到北头缫丝的声音响成一片,原来蚕农们正在紧张地劳动。这里,有枣花散落,有缫车歌唱,在路边古老的柳树下,还有一个身披牛衣的农民在卖黄瓜。“牛衣”,是一种用麻或草编成的,用来覆盖牛身的织物,这里指蓑衣一类的东西。上片三句,每一句都写出了景色的一个方面。这一次苏轼偶然来到农村,很敏感地抓住了这些特点,特别是抓住了枣花、缫丝、黄瓜这些富有时令特色的事物,把它们勾画出来。简单几笔,就点染出了一幅初夏时节农村的风俗画。
这首词,不仅是写景,还记了事。在下片,就转入了写作者自己的活动。这时他已是“酒困路长惟欲睡”。“酒困”,是酒后困倦,说明他上路前喝过酒了。“路长”,看来,已走过很长的路程,而离目的地还很远。“惟”,只。这句词写出他旅途的困倦。“日高人渴漫思茶”。“日高”,太阳已升得很高。在初夏的太阳下赶路,感到燥热、口渴,不由得想喝杯茶润喉解渴。“漫”,这里是情不自禁的意思。口渴,需要喝茶;困倦,大概也想借茶解困。于是他“敲门试问野人家”。“野人家”,乡野的人家,即乡下老百姓。苏轼当时是一州的行政长官,笔下称当地农民为“野人家”,正出于他当官的口气。但是“试问”两字表明他并没有什么官气。他没有命令随从差役去索要,而是自己亲自去敲一家老百姓的门,客气地同人家商量:老乡,能不能给一点茶解解渴呀?
就这样,用简单几句,既画出了一幅很有生活气息的农村画图;又记下了一段向老乡敲门讨茶的经历,这是他平常深居官衙中接触不到,因而感到新鲜有趣的。这首词似乎是随手写来,实际上文字生动传神,使一首记闻式的小词,获得了艺术的生命。这就是古典诗词中所讲究的“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作者为何要“敲门试问”呢?1.他是一个体恤民情、爱民如子的好父母官,谦和有礼,不会贸然闯入农家;2刚刚在旱灾后求得雨,主人可能外出下田耕作,并不在家,所以他要试探一下家中是否有人在。
《浣溪沙》词中“簌簌衣巾落枣花”一句,实为“枣花簌簌落衣巾”的倒文;杜甫《秋兴》一诗中有“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原意为: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主宾倒置的同时,宾语“香稻粒”、“碧梧枝”还被拆开分属主宾位置。对于古典诗歌诗句的倒置,清人洪亮吉说:“诗家例用倒句法,方觉奇峭生动”。
《浣溪沙》全词有景有人,有形有声有色,乡土气息浓郁。日高、路长、酒困、人渴,字面上表现旅途的劳累,但传达出的仍是欢畅喜悦之情,传出了主人公县令体恤民情的精神风貌。这首词既画出了初夏乡间生活的逼真画面,又记下了作者路途的经历和感受,为北宋词的社会内容开辟了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