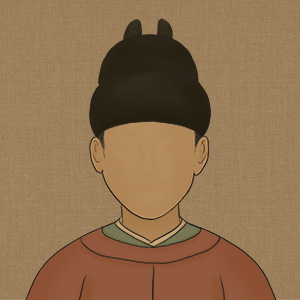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一重重缭绕的碧云深似海,在云海深处山中小路飘渺难寻觅。把几间茅屋和碧云一起租过来,碧云留在松阴上,再挂起名贵的云和八尺琴,卧在苍苔石上把云根当做枕头枕,又折下梅花拿到云梢上浸润,任运自在的云心没有常住的我,云儿和我没有半点尘念俗心。
注释
殿前欢:双调曲牌名。
赁:租赁。
云和:地名,出产琴瑟。
云和琴,指极名贵的琴。
沁:浸透。
此词为作者晚年回乡后所作。上片先写家乡南阜有小亭台,山花取次开放,婀娜多姿,因此邀请好友前开游赏,不要辜负大好春光。“多情”一词,道出了彼此间深厚的友谊。
“晴也须开,雨也须开”,表示了邀请之恳切。下片劝好友到开之后,可以开怀畅饮,随意踏青。若待天晴之后再开,则“人在天涯,春在天涯”,已经时过境迁了。全词通俗平易,流转自然。感情真挚,清新雅洁。
暮春时节,庭户寂寞,粉蝶穿槛,疏雨黄昏。东风送暖,落红成阵。此情此景,令人魂销。闺中人独自含愁,已无心肠料理玉炉香烟。这首词通过春景的描写,含蓄地透露了人物内心的离别相思之情。诗人以风华之笔,运幽丽之思。全词写得清新柔美,婉转多姿。
当春光消逝落红无数的时候,人们不免产生一种怅惘的心绪。莺歌燕舞、姹紫嫣红的春光给人带来生活的欢乐和美的享受,也悄悄带走人的青春年华。这首词在暮春时节风雨花飞的背景下,抒写闺中春愁,它所蕴含的春思清韵,别有一番耐人寻味的意蕴。上阕写晚天疏雨、粉蝶双飞。一般地说,春天的蜂儿蝶儿,多在日间和风日丽的花树丛中穿飞。而作者笔下的双双粉蝶,偏于晚天疏雨中穿槛而飞,其点缀寂寞庭户,反衬闺中人孤独境况的用心,不言而谕,粉蝶双飞本是无意,但在有情人的心中,顿起波澜,牵动春思:她对青春幸福的向往,对爱人的期待,通过这对比鲜明的画面暗示给读者。下阕写闺中人在期待中的失望。晚天疏雨中,天气微寒,她独倚帷帐双眸含愁,任“玉炉烟断香微”。只是当帘外闲庭中东风摇荡花树,满树花飞如雨的景象才将她从痴迷中唤醒,春光匆匆归去,不禁使她销魂荡魄。
毛熙震是花间派词人,但这首词的写景状物多用白描,清丽疏淡,情味蕴藉,与“花间”秾丽香艳、镂金错彩的风格迥异。作者写的闺中人,不描摹其体态衣妆,不明言其多愁善感,除了“含愁”一句正面点明其期待与失望,再以“玉炉”一句烘托其期待已久,相思之苦,其余各句,均于景物描写中带出她的形影与神态,这正是词论家所称道的融情入景的功力。词中所摄取的双飞的粉蝶、晚天疏雨、东风花树等景物,是最富于表现暮春清韵和闺中人春愁的典型景物,将它们和谐地组合起来,使全词有了直观的画面,具有诱人的美感,情景交融,了无痕迹。前人论词的章法,讲究“短章蕴藉”,言尽意不尽。此词就是一首情景相生、含蓄蕴藉的佳作。它那情在言外的意蕴,比起痛快淋漓的表白,更具有耐人寻味的魅力。尤其篇末“东风满院花飞”一句,形象凄艳,含蕴无穷。
其一
此诗通过送荔枝这一典型事件,鞭挞了玄宗与杨贵妃骄奢淫逸的生活,有着以微见著的艺术效果,精妙绝伦,脍炙人口。
起句描写华清宫所在地骊山的景色。诗人从长安“回望”的角度来写,犹如电影摄影师,在观众面前先展现一个广阔深远的骊山全景:林木葱茏,花草繁茂,宫殿楼阁耸立其间,宛如团团锦绣。“绣成堆”,既指骊山两旁的东绣岭、西绣岭,又是形容骊山的美不胜收,语意双关。
接着,场景向前推进,展现出山顶上那座雄伟壮观的行宫。平日紧闭的宫门忽然一道接着一道缓缓地打开了。接下来,又是两个特写镜头:宫外,一名专使骑着驿马风驰电掣般疾奔而来,身后扬起一团团红尘;宫内,妃子嫣然而笑了。几个镜头貌似互不相关,却都包蕴着诗人精心安排的悬念:“千门”因何而开?“一骑”为何而来?“妃子”又因何而笑?诗人故意不忙说出,直至紧张而神秘的气氛憋得读者非想知道不可时,才含蓄委婉地揭示谜底:“无人知是荔枝来。”“荔枝”两字,透出事情的原委。《新唐书·杨贵妃传》:“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明于此,那么前面的悬念顿然而释,那几个镜头便自然而然地联成一体了。
吴乔《围炉诗话》说:“诗贵有含蓄不尽之意,尤以不著意见声色故事议论者为最上。”杜牧这首诗的艺术魅力就在于含蓄、精深,诗不明白说出玄宗的荒淫好色,贵妃的恃宠而骄,而形象地用“一骑红尘”与“妃子笑”构成鲜明的对比,就收到了比直抒己见强烈得多的艺术效果。“妃子笑”三字颇有深意。春秋时周幽王为博妃子一笑,点燃烽火,导致国破身亡。读到这里时,读者是很容易联想到这个尽人皆知的故事。“无人知”三字也发人深思。其实“荔枝来”并非绝无人知,至少“妃子”知,“一骑”知,还有一个诗中没有点出的皇帝更是知道的。这样写,意在说明此事重大紧急,外人无由得知,这就不仅揭露了皇帝为讨宠妃欢心无所不为的荒唐,也与前面渲染的不寻常的气氛相呼应。全诗不用难字,不使典故,不事雕琢,朴素自然,寓意精深,含蓄有力,是唐人咏史绝句中的佳作。
其二
唐玄宗时,安禄山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后伺机谋反,玄宗却对他十分宠信。皇太子和宰相杨国忠屡屡启奏,方派中使辅璆琳以赐柑为名去探听虚实。璆琳受安禄山厚赂,回来后盛赞他的忠心。玄宗轻信谎言,自此更加高枕无忧,恣情享乐了。“新丰绿树起黄埃,数骑渔阳探使回”,正是描写探使从渔阳经由新丰飞马转回长安的情景。这探使身后扬起的滚滚黄尘,是迷人眼目的的烟幕,又象征着叛乱即将爆发的战争风云。
诗人从“安史之乱”的纷繁复杂的史事中,只摄取了“渔阳探使回”的一个场景,是颇具匠心的。它既揭露了安禄山的狡黠,又暴露了玄宗的糊涂,有“一石二鸟”的妙用。
如果说诗的前两句是表现了空间的转换,那么后两句“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则表现了时间的变化。前后四句所表现的内容本来是互相独立的,但经过诗人巧妙的剪接便使之具有互为因果的关系,暗示了两件事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从全篇来看,从“渔阳探使回”到“霓裳千峰上”,是以华清宫来联结,衔接得很自然。这样写,不仅以极俭省的笔墨概括了一场重大的历史事变,更重要的是揭示出事变发生的原因,诗人的构思是很精巧的。
将强烈的讽刺意义以含蓄出之,尤其是“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两句,不着一字议论,便将玄宗的耽于享乐、执迷不悟刻画得淋漓尽致。说一曲霓裳可达“千峰”之上,而且竟能“舞破中原”,显然这是极度的夸张,是不可能的事,但这样写却并非不合情理。因为轻歌曼舞纵不能直接“破中原”,中原之破却实实在在是由统治者无尽无休的沉醉于歌舞造成。而且,非这样写不足以形容歌舞之盛,非如此夸张不能表现统治者醉生梦死的程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国破家亡的严重后果。此外,这两句诗中“千峰上”同“下来”所构成的鲜明对照,力重千钧的“始”字的运用,都无不显示出诗人在遣词造句方面的深厚功力,有力地烘托了主题。正是深刻的思想内容与完美的表现手法,使之成为脍炙人口的名句。全诗到此戛然而止,更显得余味无穷。
其三
这是三绝句中的最后一首,也是一首讽喻诗。
“万国笙歌醉太平”,此言唐玄宗整日与杨贵妃在骊山游乐,不理朝政,举国上下也沉浸在一片歌舞升平之中。“倚天楼殿月分明”,此言骊山上宫殿楼阁高耸挺拔,在月光下显得格外分明。“云中乱拍禄山舞”,此句语带讥刺地说:想当年安禄山在骊山上觐见唐玄宗和杨贵妃时,在大殿中拖着肥胖的身体翩翩作胡旋舞,竟引发了杨贵妃爽朗的笑声。“风过重峦下笑声”,此言那笑声随风飘扬越过层层峰峦,在山间久久回荡。
据载:杨贵妃见安禄山作胡旋舞,心花怒放,竟收安禄山做自己的干儿子,唐玄宗也非常高兴,对安禄山分外器重,委任他为三镇节度使。但恰恰是他们的这位干儿子对他们举起了反叛的大旗。大唐帝国也从此滑向衰亡的深渊。
此诗含蓄委婉,笔调看似轻快,实则对亡国之君的荒淫误国给予了辛辣无情的嘲讽。
纳兰这首词与他其他的赠友词有所不同,这一次他没有一味地抒发怀念,而是侧重叙志。“问我何心?却构此、三楹茅屋。”这话问得蹊跷。在风景秀丽的渌水亭旁边修几间中看不中用的茅屋,是烧钱多。所以,这样的问题,很没有建设性的水准,但句子却是相当的流畅、明了。 接着是回答。有问有答,态度很端正。纳兰自圆其说,可以闲居于此,就像自由自在的海鸥那样,无忧无虑,自得其乐。古代人喜欢用与海鸥为伴表示闲适或隐居。宋代陆游《雨夜怀唐安》诗中有“小阁帘栊频梦蝶,平湖烟水已盟鸥”句,用庄生梦蝶和鸥鸟订盟的典故来喻示闲适的生活。纳兰淡泊功名,向往过着陶渊明等隐居标兵不问世事的悠闲生活。 “百感都随流水去,一身还被浮名束。”这里是看破红尘的觉悟。生命如水,忙忙碌碌之间,一切都已经流逝。所有才情,所有的雄心壮志都将被风雨吹打得七零八落,而我岂能还为虚妄的功名利禄所缚?
朱颜青鬓,枉被浮名误!生活的底蕴究竟是什么?是既然生下来了,就要活下去吗?几千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一代又一代人。有的追名逐利,有的独善其身,有的寄情山水,有的烧香拜佛,有的舍生取义,有的苟且偷生。
上片最后一句“红牙曲”指拍击着红牙板歌唱。红牙板是用红色檀木制成,古代于唱歌时打拍子用的牙板,与北方说“数来宝”的艺人手中所持的碎板有些类似,只是木质更好、做工更细而已。元代诗人杨维桢专有一首《红牙板》诗,描绘说:“良工削出红冰片,自非红鸾之舌为尔绳,安得三三贯成串?”
下片点出所以要摆脱“浮名束”的原因,设想如何打发今后的生活。如今世事反复无常,当袖手旁观,将其作为一局棋来看待。蕉中鹿,有世事无常、真假难分的意思。典出《列子》:有一个郑国人砍柴时,忽见一只鹿跑过来,他一扁担将鹿打死。他怕被猎人看见,将鹿藏在一个坑里,上面盖上一些蕉叶。等到他要将鹿带回家时,却找不到了,就以为这是一个梦,一路自言自语,被路旁一个人听到了,这个路人好奇地依言找到了这只鹿。樵夫回到家里,不甘心失掉这只鹿,夜里真的又梦见他藏鹿的地方,还梦见拿走鹿的那个人。第二天清早,樵夫就根据他梦中的线索找到了那个人。于是两个人为争鹿起诉,闹到了法官那里。这个故事形容世间事物真伪难辨,得失无常。
既然世事无常,何不躲避在一边,纵酒吟诗,自在悠闲,也算是安享一份微薄的福气。
大雪之后屋檐角闪烁的那一丁点儿翠绿,雨后靠墙栽种的绿苗,寒夜里摇曳的灯烛——这,就是纳兰期望的生活意趣,他渴望摆脱宦海羁绊,避开现实去过田园的悠闲生活。
宋廷南迁,围绕定都问题,有过一段时期的争论。
建炎三年(1129)二月,帝在镇江。当时金军正拟渡江南下,帝召从臣问计,王渊以杭州有重江之险,主张逃往杭州。高宗畏敌如虎,此话正中下怀。张邵上疏曰:“今纵未能遽争中原,宜进都金陵,因江、淮、蜀、汉、闽、广之资,以图恢复。”帝不听,去了杭州。绍兴六年(1136)七月,张浚上奏曰:“东南形胜莫重于建康(即金陵),实为中兴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怀愤惕,不敢暇逸。而临安(即杭州)僻在一隅,内则易生玩肆,外则不足以号召远近,系中原之心。请临建康,抚三军,以图恢复。”这一回因形势好转,即于次年移跸金陵。但八年回杭州。张守谏曰:“建康自六朝为帝王都,气象雄伟,且据都会以经理中原,依险阻以捍御强敌。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军有勤动之苦,民力邦用有烦费之忧。愿少安于此,以系中原民心。”然而高宗正一心与金人议和不以收复北方失地为大业,执意定都杭州。同年,宋金签订了“绍兴和议”,自此南宋都定临安。(见《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南迁定都》)康与之此词,正即作于这一历史时期。名曰“怀古”,实是“伤今”,是针对当时南宋小朝廷奉行逃跑和妥协政策而发的扼腕之叹。
上阕思接千载,写历史长河中的金陵。金陵群山屏障,大江横陈,是东南形胜之地,自三国吴孙权建都于此,历东晋、宋、齐、梁、陈,六朝为帝王之宅,豪华竞逐,盛极一时。起二句,即概述那一段灿烂辉煌的往事,以先声夺人。“龙蟠虎踞”四字用典,汉末诸葛亮出使东吴,睹金陵(时称秣陵)山阜,有“钟山龙蟠,石头虎踞”之见,见《太平御览。州郡部。叙京都》引晋张勃《吴录》。南京山川雄伟人事繁华,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然而,宇宙无穷,山川长在;盈虚有数,人事不居。三百馀年在永恒的历史面前只是弹指一瞬。随着政权更迭,国都无移,金陵的繁华已成古迹。“缥凤”二句,情绪陡落千丈,与后蜀欧阳炯《江城子》(晚日金陵岸草平)之所谓“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北宋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之所谓六朝旧事随流水”同一感慨。由字面可看出,明显是化用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缥凤,淡清色的凤鸟。凤凰台,故址在今南京花盝冈。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有三鸟翔集于此,状如孔雀,五色文彩,鸣声谐和,众鸟群至,遂筑此台以纪其瑞。见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升州·江宁县》。由于李白诗为人们所熟知,而读者不难联想而及同诗中“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等名句,局部返观为整体,十个字带出了一连串意境,当年“豪华”之盛,今日萧瑟之衰,种种画面遂一而过。且“龙蟠虎踞”云云以“山”起,“台空江流”云云以“水结”针缕亦极周到。
题面“金陵怀古”之意,上阕四句已足。然词人之用心原不在“发思古之幽情”,为“怀古”而“怀古”,“怀古”的目的是为了“伤今”,故下阕即转入此旨。“下临”二句,视通万里,置金陵于有利战略地位。“全楚地”,语见唐刘长卿《长沙馆中与郭夏对雨》诗“云横全楚地”,泛指长江中游地区。春秋战国时,此系楚国的腹地,故云。“包举”,包抄而攻取。二句说金陵为长江下游的战略要地,与长江中游诸重镇共同构结成包抄中原的态势。按当时军事方略,南宋如欲北伐收复中原失地,可于长江中、下游两路出兵,一路自鄂州(今武汉市一带)出荆襄,直趋河路;一路自金陵等地出淮南,迂回山东。倘若更置一军自汉中出,攻取关陕,三路进击,则尤佳。词人能够高度评价金陵在北伐事业中所占据的重要战略地位,见识卓越前引张邵、张浚、张守之奏议,与康与之此词,或为政治家之言论,或为文学家之笔墨,都代表着当时的军心、民心。南宋爱国词,与民族、人民的愿望息息相通。行文至此,词情再度振起。可是,“事无两样人心别”(辛弃疾《虞美人。同父见和再用前韵》),以高宗为首的南宋统治集团只知向金人屈膝求和,不知利用民众力量。他们龟缩在浙东一隅,视长江天险为第二道院墙,不去利用金陵的战略位置。
面对这一冷酷的现实,词人的激情不禁再一次跌到冰点。“可惜草连天,晴郊狐兔眠!”一声长吁,包含着多么沉重的失望与痛苦啊。作为南宋臣民,词人不可能直言不讳地去批揭那龙喉下的逆鳞,然而他已经形象地告诉后人,南宋统治者的胆识,在六朝之下!东晋以迄梁陈,文治武功虽不甚景气,毕竟尚有勇气定都金陵,与北方抗衡,未至于躲得那么远呢。
此词的特点是,上下八句,两两相形,共分为四个层次,呈现为“扬——抑——扬——抑”的大起大落,这种章法与词人怀古伤今时起伏的心潮吻合无间。
由起句的“龙蟠虎踞”到收句的“狐卧兔眠”,两组意象遥遥相对,亦是匠心所在。其意盖从北周庚信《哀江南赋》“昔之虎踞龙盘,加以黄旗紫气,莫不随狐兔而窟穴,与风尘而殄瘁”云云化出,更为简洁。龙虎地而无有龙腾虎掷的形象,却成为狐兔之乐园,此情此景,本身即是莫大的讽刺,不必更着一字,读者已随词人作喟然之浩叹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