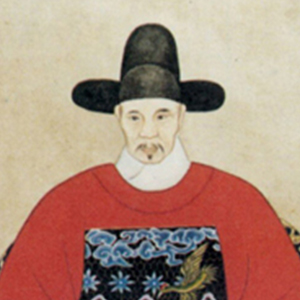该诗写诗人登上军事要地丁家洲追思往昔,刻写奸臣无能误国,抒发了山河家国的情怀。
诗歌说,当年太师贾似道统领十余万人马,抵抗南侵的元军,煞有介事,而人们似乎也天真地抱持以强烈的希望。然而,惊若沙鸥、畏敌如虎的宋军,一听到元军吹起的号角,即已溃不成军,一溃再溃,直到扬州登岸。可是事情并没有完,贾似道仍然故技重施,摇旗呐喊,招集残兵。此情此景,还有多少人相信贪生怕死的奸臣还能拯家救国的道理,但见江船里,士兵的咒骂声连成一片。到处弥漫着逃跑、退缩、内讧与败亡的气息。结果一次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却滑变成了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于是诗歌讥刺与冷嘲的意味,便流溢而出。
注释
注释
笳:胡笳,这里指元军的号角。
惊若鸥:形容畏敌的宋军。
赢得:落得、剩得。
该诗写诗人登上军事要地丁家洲追思往昔,刻写奸臣无能误国,抒发了山河家国的情怀。
诗歌说,当年太师贾似道统领十余万人马,抵抗南侵的元军,煞有介事,而人们似乎也天真地抱持以强烈的希望。然而,惊若沙鸥、畏敌如虎的宋军,一听到元军吹起的号角,即已溃不成军,一溃再溃,直到扬州登岸。可是事情并没有完,贾似道仍然故技重施,摇旗呐喊,招集残兵。此情此景,还有多少人相信贪生怕死的奸臣还能拯家救国的道理,但见江船里,士兵的咒骂声连成一片。到处弥漫着逃跑、退缩、内讧与败亡的气息。结果一次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却滑变成了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于是诗歌讥刺与冷嘲的意味,便流溢而出。
李昌祺是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他二十九岁成进士,入仕途,居官北京和广西、河南,到六十多岁才告老归家,一生游宦三十多年。古人重乡土。在外地的日子越长,越是怀念故乡,一旦能晤乡人,即使彼此素不相识,也觉得特别亲热,有说不完的话。李昌祺活了七十多岁。当他老年居官异地时,故乡的许多亲朋已经谢世;由于当时交通不便,音书梗阻,这些人的消息他无法一一知道;一旦听到故乡来人说起,老人便不禁伤心泪落,不忍卒听。这首小诗写的就是这种心情。诗中“故旧凭君休更说”的“凭”是请求的意思,“凭君”犹言“请你”,唐宋诗词中常用此义。
不忍心听故旧死亡的消息,是老年人共同的心态。一来,人到老年,心多慈软,不能承受这种刺激;二来,故旧飘零,往往勾起老人许多辛酸往事,陷入复杂痛苦的回忆中,容易引起感伤;再则,亲朋一个个死了,他这位幸存者能不想到自己的来日无多吗?对此,年龄越大的人,越发敏感。因此,这首诗抒发的是人之常情,具有广泛的典型意义。
但是,有趣的是:故旧死亡的消息老人不忍闻,故乡的近事老人却特别想听,哪怕只是一丘一壑的变迁,一时一事的兴革。诗把这两种心情写得非常生动突出。“形容不识识乡音,挑尽寒灯到夜深”:来的这位乡人,尽管老人从不认识,但他那满口乡土语音,老人听来却格外熟悉,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长期在广西、河南游宦,几曾听到过江西吉安人的口音?贺知章说:“乡音无改鬓毛衰”,乡音是一种特殊的乡土文化的印记;在天涯异域,听到乡音便倍感亲切,彼此的心自然靠近了,而且有了共同的话题。今晚,这话题是那样富于吸引力,把老人带入了色彩斑斓的世界。天尽管寒冷,夜尽管深沉,老人却听得津津有味,挑尽寒灯,毫无倦容。诗句对此只作了平静的叙述,我们却借着那“寒灯”的微光,看见了这位老人兴奋的脸色,激动的童心。
于是我们看到:这首小诗揭示了一种有趣的矛盾心态——又是爱听,又是怕听。“爱听”的心情,通过“挑尽寒灯”四字写得盎然欲滴,老人仿佛小孩瞪着大眼,托着腮帮子听人讲故事一样,形象十分鲜明。“怕听”的心情,通过“凭君”二字,也显得深沉迫切,老人的形象又变得皱纹满脸,灯光下老泪纵横。正是这种有趣的矛盾,这种前后截然不同的形象,使这首小诗充满了喜剧情调。你读着它,将止不住发出幑再一想,又不禁感到凄然。
更值得一提的是:诗写得如此自然浑成,你找不到什么“诗眼”,也找不到什么“警句”,诗人只是叙写了这次夜话的过程,他只是顺着生活的本来面目来写一己之哀乐,却无意之中表现出了老年人的普遍的心态,勾画出从童心盎然到老怀凄怆的形象变化。诗,真有不可思议的魅力!
这首小令前三句点明主旨,分别从空间和时间,极言家乡路途遥远。中间三句皆是作者的眼前之景,无不映照着他那颗伤感的旅人之心。最后两句写各种声音交织一起化作离愁,致使作者一夜无眠。全曲缠绵悱恻,呜咽低回,读来令人哀愁如缕,感叹不已。
“故园一千里,孤帆数日程”,小令开篇即直写故乡的遥远和行旅的孤寂,从而引出第三句“倚篷窗自叹飘泊命”的深沉喟叹,“城头鼓声,江心窗声,山顶钟声”三句,表面上全是写景,然一片孤寂烦闷之情,却寓于这“鼓声”、“窗声”、“钟声”之中。这是一种以动写静的手法,独自一人在孤舟之中,又是夜深的江上,孤独寂寞之情是可想而知的。静极时,便越发显得这“鼓声”、“窗声”、“钟声”的响亮。反过来,这声音也越发显得夜深江上的寂静。此情此景搅起了游子的无限身世之感与思乡之情,以至再也按捺不住这一腔愁绪,便冲口而出“一夜梦难成,三处愁相并”。
全篇寓情于景,以景衬情,渲染寂寞悲凉的气氛,表达了失意惆怅的情怀。四、五、六三句,语气平淡而意蕴隽永。“城头鼓声”,暗示时光流逝,使人易生光阴蹉跎的感慨,“江心窗声”,象征人生旅途的险恶,使人感发“世途风波恶,人间行路难”的浩叹;“山顶钟声”,则显然和唐代诗人张继所听到的寒山寺夜半钟鸣一样,使人深感客中的凄凉和惆怅。这三种声音,构成一部情调悲凉的交响乐章,发人遐想。另外,曲词的语言朴实而凝炼,工整而有节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