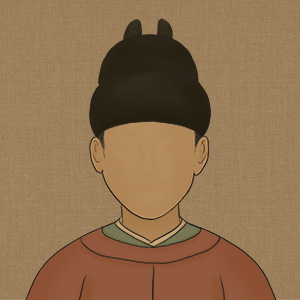此词描绘了一个女子思念爱人的痛苦心情,读来凄婉动人。古人对它评价很高,把它与《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一起誉为“百代词曲之祖”。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词人落笔就写一个京城女子,在一个月照高楼的夜晚,被凄凉呜咽的箫声惊醒了好梦。“秦娥”,泛指京城长安的一个美丽的女子。《方言》卷二云:“秦晋之间,美貌谓之娥。”“梦断”,谓梦被箫声所惊醒。这里反用《列仙传》所载萧史与弄玉的故事,因为善吹箫的萧史被秦穆公的女儿爱上,终于结为夫妻,一起随凤飞去,那该是多么美好;可这位秦娥呢,单身独宿,只能在梦中与爱人相聚,偏偏好梦被那凄切箫声所打断,醒来一看空剩清冷的月色,心里又该是多么悲伤!一个“咽”字,渲染出境界之凄凉;一个“断”字,烘托出秦娥内心的失望。开头两句就这样以流丽之艳语而描写出哀婉欲绝之情思。
“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秦娥从梦中惊醒,眼前只有照着楼台的月色;借着月色向楼下看,只见杨柳依旧青青,一如既往,不禁勾起往年在灞桥折柳,送别爱人那种悲伤情景的回忆。“秦楼月”之反复,本是这个词调的要求;而在这首小令之中,不仅起到由月色而见柳色的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加强了对于孤独凄凉的环境气氛的渲染。至于由“柳色”而跳跃到“伤别”上去,既是从汉代以来折柳送别这一传统风尚生发出来的想象,又是对秦娥怀念远人心情的进层刻画。“灞陵”,汉文帝刘恒的陵墓,在今陕西西安市东,附近有灞桥,为长安人士送别之所。《三辅黄图》云:“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灞陵”一作“灞桥”。“灞陵伤别”,是由柳色触发的对当时分别情景的回忆,它既补明了“梦断”之“梦”乃是与远别爱人相聚的好梦,更为下阕结句的描写埋下了伏笔。这一“伤别”,本写秦娥之离愁别恨,而以年年贯之,则把多少年、多少代人间共有的悲剧连类道尽,境界顿然阔大起来,赋予了普遍的意义。这三句连贯而下,层层浮想,句意跳跃,脉络相承,曲尽秦娥梦断之后的所见和所思。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这两句紧承“伤别”,描写秦娥登原望信而不得的景象。“乐游原”在今西安市南,居全城最高处,四望宽敞,可瞭望全城和周围汉朝的陵墓;这里写秦娥登临远望的地点。“清秋节”,点明是清凉的秋季,既补写上阕没有明写的时间,又点染冷清寂寥的气氛。此时此地,秦娥满怀愁绪,眼望爱人由此离去的咸阳古道,苦苦等着,然而尘埃不起,音信全无。“咸阳”,乃秦朝京城,至汉、唐时从京城长安往西北经商或从军,咸阳为必经之地;“古道”,年代久远的通道,一个“古”字唤起人们对古往今来多少过客的不尽联想,前人喻之“语境则‘咸阳古道’”(引江顺诒《词学集成》),正说出其境界之寥廓。“音尘绝”,见于蔡琰《胡笳十八拍》之十:“故乡隔兮音尘绝,哭无声兮气将咽。”“音尘”本谓声音与尘埃,后借指信息;“绝”,断绝。这三字,不仅写尽咸阳古道寂静冷落的景象,更把秦娥孤独无望、欲哭无声的心境写绝,其“伤别”之情可谓极矣!
“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词人依词调的要求,将“音尘绝”三字加以反复,进一步强调从乐游原上远望咸阳古道的悲凉景象,和秦娥哀婉凄切的心境,而引出秦娥眼前之所见,只有在肃杀的秋风之中,一轮落日空照着汉代皇帝陵墓的荒凉图景。“阙”,此指陵墓前的牌楼。汉朝皇帝的陵墓都在长安周围(详见《三辅黄图》),而身登乐游原的秦娥凭高瞭望,不见音尘,正将此景尽收眼底,同时秦娥怀古伤今的弦外之音,也借此被表达得淋漓尽致。特别是这结尾两句与上阕的结尾两句前后照应,从年年伤别的怀念远人,到残照陵阙的怀古伤今,气象突然为之开阔,意境也就愈显深远。
此词意境博大开阔,风格宏妙浑厚。读者从敦煌曲子词中也可以看到类似格调,而不类中晚唐的清婉绮丽。陆游说:“唐自大中以后,诗家日趋浅薄,其间不复有前辈宏妙浑厚之作。”(《花间集跋》)。诗风与词风自身存在着交错否定之趋势。
此词句句自然,而字字锤炼,沉声切响,掷地真作金石声。而抑扬顿挫,法度森然,无字荒率空泛,无一处逞才使气。以此而言,设为李太白之色,毋宁认是杜少陵之笔。其风格诚在五代花间未见,亦非歌席诸曲之所能拟望,已开宋代词之格调。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玉箫的声音悲凉呜咽,秦娥从梦中惊醒时,眼见秦家楼外一轮清冷明月。清冷的明月,每一年桥边青青的柳色,都印染着灞陵桥上的凄怆离别。
又是一年重阳佳节,登上乐游原,秦娥遥望咸阳古道,可叹那人了无影踪、音信断绝。良人不见啊音信断绝,只有西风萧瑟,残阳似血,拂照着那汉家帝王的陵阙。
注释
箫:一种竹制的管乐器。
咽:呜咽,形容箫管吹出的曲调低沉而悲凉,呜呜咽咽如泣如诉。
梦断:梦被打断,即梦醒。
灞陵: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是汉文帝的陵墓所在地。当地有一座桥,为通往华北、东北和东南各地必经之处。
伤别:为别离而伤心。
乐游原:又叫“乐游园”,在长安东南郊,是汉宣帝乐游苑的故址,其地势较高,可俯视长安城,在唐代是游览之地。
清秋节:指农历九月九日的重阳节,是当时人们重阳登高的节日。
咸阳古道:咸阳,秦都,在长安西北数百里,是汉唐时期由京城往西北从军、经商的要道。古咸阳在今陕西省咸阳市东二十里。唐人常以咸阳代指长安,“咸阳古道”就是长安道。
音尘:一般指消息,这里是指车行走时发出的声音和扬起的尘土。
残照:指落日的光辉。
汉家:汉朝。
陵阙:皇帝的坟墓和宫殿。
此词描绘了一个女子思念爱人的痛苦心情,读来凄婉动人。古人对它评价很高,把它与《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一起誉为“百代词曲之祖”。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词人落笔就写一个京城女子,在一个月照高楼的夜晚,被凄凉呜咽的箫声惊醒了好梦。“秦娥”,泛指京城长安的一个美丽的女子。《方言》卷二云:“秦晋之间,美貌谓之娥。”“梦断”,谓梦被箫声所惊醒。这里反用《列仙传》所载萧史与弄玉的故事,因为善吹箫的萧史被秦穆公的女儿爱上,终于结为夫妻,一起随凤飞去,那该是多么美好;可这位秦娥呢,单身独宿,只能在梦中与爱人相聚,偏偏好梦被那凄切箫声所打断,醒来一看空剩清冷的月色,心里又该是多么悲伤!一个“咽”字,渲染出境界之凄凉;一个“断”字,烘托出秦娥内心的失望。开头两句就这样以流丽之艳语而描写出哀婉欲绝之情思。
“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秦娥从梦中惊醒,眼前只有照着楼台的月色;借着月色向楼下看,只见杨柳依旧青青,一如既往,不禁勾起往年在灞桥折柳,送别爱人那种悲伤情景的回忆。“秦楼月”之反复,本是这个词调的要求;而在这首小令之中,不仅起到由月色而见柳色的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加强了对于孤独凄凉的环境气氛的渲染。至于由“柳色”而跳跃到“伤别”上去,既是从汉代以来折柳送别这一传统风尚生发出来的想象,又是对秦娥怀念远人心情的进层刻画。“灞陵”,汉文帝刘恒的陵墓,在今陕西西安市东,附近有灞桥,为长安人士送别之所。《三辅黄图》云:“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灞陵”一作“灞桥”。“灞陵伤别”,是由柳色触发的对当时分别情景的回忆,它既补明了“梦断”之“梦”乃是与远别爱人相聚的好梦,更为下阕结句的描写埋下了伏笔。这一“伤别”,本写秦娥之离愁别恨,而以年年贯之,则把多少年、多少代人间共有的悲剧连类道尽,境界顿然阔大起来,赋予了普遍的意义。这三句连贯而下,层层浮想,句意跳跃,脉络相承,曲尽秦娥梦断之后的所见和所思。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这两句紧承“伤别”,描写秦娥登原望信而不得的景象。“乐游原”在今西安市南,居全城最高处,四望宽敞,可瞭望全城和周围汉朝的陵墓;这里写秦娥登临远望的地点。“清秋节”,点明是清凉的秋季,既补写上阕没有明写的时间,又点染冷清寂寥的气氛。此时此地,秦娥满怀愁绪,眼望爱人由此离去的咸阳古道,苦苦等着,然而尘埃不起,音信全无。“咸阳”,乃秦朝京城,至汉、唐时从京城长安往西北经商或从军,咸阳为必经之地;“古道”,年代久远的通道,一个“古”字唤起人们对古往今来多少过客的不尽联想,前人喻之“语境则‘咸阳古道’”(引江顺诒《词学集成》),正说出其境界之寥廓。“音尘绝”,见于蔡琰《胡笳十八拍》之十:“故乡隔兮音尘绝,哭无声兮气将咽。”“音尘”本谓声音与尘埃,后借指信息;“绝”,断绝。这三字,不仅写尽咸阳古道寂静冷落的景象,更把秦娥孤独无望、欲哭无声的心境写绝,其“伤别”之情可谓极矣!
“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词人依词调的要求,将“音尘绝”三字加以反复,进一步强调从乐游原上远望咸阳古道的悲凉景象,和秦娥哀婉凄切的心境,而引出秦娥眼前之所见,只有在肃杀的秋风之中,一轮落日空照着汉代皇帝陵墓的荒凉图景。“阙”,此指陵墓前的牌楼。汉朝皇帝的陵墓都在长安周围(详见《三辅黄图》),而身登乐游原的秦娥凭高瞭望,不见音尘,正将此景尽收眼底,同时秦娥怀古伤今的弦外之音,也借此被表达得淋漓尽致。特别是这结尾两句与上阕的结尾两句前后照应,从年年伤别的怀念远人,到残照陵阙的怀古伤今,气象突然为之开阔,意境也就愈显深远。
此词意境博大开阔,风格宏妙浑厚。读者从敦煌曲子词中也可以看到类似格调,而不类中晚唐的清婉绮丽。陆游说:“唐自大中以后,诗家日趋浅薄,其间不复有前辈宏妙浑厚之作。”(《花间集跋》)。诗风与词风自身存在着交错否定之趋势。
此词句句自然,而字字锤炼,沉声切响,掷地真作金石声。而抑扬顿挫,法度森然,无字荒率空泛,无一处逞才使气。以此而言,设为李太白之色,毋宁认是杜少陵之笔。其风格诚在五代花间未见,亦非歌席诸曲之所能拟望,已开宋代词之格调。
此诗四章,每章四句,各章前两句均为起兴,且兴词紧扣下文事象:宴饮是在夜间举行的,而大宴必至夜深,夜深则户外露浓;宗庙外的环境,最外是萋萋的芳草,建筑物四围则遍植杞、棘等灌木,而近户则是扶疏的桐、梓一类乔木,树木上且挂满果实——此时一切都笼罩在夜露之中。
“白露”“寒露”为农历八、九月之节气,而从夜露甚浓又可知天气晴朗,或明月当空或繁星满天,户厅之外,弥漫着祥和的静谧之气;户厅之内,则杯觥交错,宾主尽欢,“君曰:‘无不醉’,宾及卿大夫皆兴,对曰:‘诺,敢不醉!’”(《仪礼·燕礼》)内外动静映衬,是一幅绝妙的“清秋夜宴图”。
若就其深层意蕴而言,宗庙周围的丰草、杞棘和桐椅,也许依次暗示血缘的由疏及亲;然而更可能是隐喻宴饮者的品德风范:既然“载考”呼应“丰草”,“载”义为充盈,而“丰”指繁茂,那么“杞棘”之有刺而能结实不可能与君子的既坦荡光明(显)又诚悫忠信(允)无涉,更不用说桐椅之实的“离离”——既累累繁盛又历历分明——与君子们一个个醉不失态风度依然优美如仪(与《小雅·宾之初筵》的狂醉可对看)的关系了。只是至此还没有说到最重要的意象“湛湛”之“露”究属何意。
前人大多理解湛露既然临于草树,则无疑象征着王之恩泽。若就二、三章而言,这也不差,只是以之揣摩首章,却不像了。露之湛湛其义蕴犹情之殷殷,热情得酒之催发则情意更烈,正好比湛露得朝阳则交汇蒸腾。
此诗章法结构之美既如陈奂所言“首章不言露之所在,二章三章不言阳,末章并不言露,皆互见其义”,又如朱熹引曾氏曰:“前两章言厌厌夜饮,后两章言令德令仪”。后者需补充的是:在这两者之间,第三章兼有过渡性质(一、二承上,三、四启下)。雅诗的章法结构比风诗更为讲究,于此亦见一斑。
音韵的谐美也是此诗一大特点:除了隔句式押韵外,前两章以一、三句句头的“湛湛”与“厌厌”呼应,去和二、四句句尾的脚韵共构成回环之美;至后两章则改为顶真式谐音,表现为“杞棘”的准双声与“显允”的准叠韵勾连,而“离离”的双叠也与“岂弟”的叠韵勾连(作为过渡,三章“湛湛”与“显允”的尾音也和谐呼应)。
这首诗评论江西诗派。宋人是推崇学习杜甫的,而李商隐的能得杜甫遗意,学杜要先学李商隐,宋人早具有此说法。在元好问看来,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虽然标榜学杜,但并未抓住杜诗的真髓,而专在文字、对偶、典故、音韵等形式上模拟因袭,结果既未学到杜诗的古朴风雅得真谛,也完全失去了李商隐的精美纯厚的风格。因此他明确表示,不愿与江西诗派为伍,不愿拾江西诗派的牙唾。
但是,这里元好问对于黄庭坚的态度怎样呢,关键是“宁”字的理解。教材P285注释57解释为“岂能”。也有不同理解,下面介绍一下周振甫、冀勤编注钱钟书《谈艺录》的《〈谈艺录〉读本》中“鉴赏论第七”:
《谈艺录》(七)元好问论黄庭坚诗解:遗山诗中“宁”字,乃“宁可”之意,非“岂肯”之意。如作“岂肯”解,则“难将”也,“全失”也,“宁下”也,“未作”也,四句皆反对之词,偏面复出,索然无味。作“宁可”解,适在第三句,起承而转,将合先开,欲收故纵,神采始出。其意若曰:“涪翁虽难亲少陵之古雅,全失玉溪之精纯,然较之其门下江西派作者,则吾宁推涪翁,而未屑为江西派也”:是欲抬山谷高出于其弟子。然则江西派究何如。乃紧接下一绝曰:“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盖举后山以概其余西江诗人,此外比诸郐下,不须品题。遂系以自述一首,而《论诗绝句》终焉。《遗山集》中于东坡颇推崇,《杜诗学引》称述其父言:“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而《论诗绝句》伤严寡恩如彼,倘亦春秋备责贤者之意。遗山所深恶痛绝,则为江西派,合之《中州集自题》绝句,更彰彰可见。(153页)
《〈谈艺录〉读本》注解:这一则讲元好问《论诗》中论黄庭坚的诗:“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钱先生先抓住“宁”字来讲,认为是“宁可”的“宁”,即宁可向黄庭坚拜倒,不作江西诗派中人。即把黄庭坚突出于江言诗派以外,认为黄庭坚还是可取的。虽然黄庭坚的诗不如杜甫诗的古雅,全失李商隐诗的精纯,但还是好的。元好问为什么要向黄庭坚下拜,在《论诗》里没有说。《论诗》说的“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称谢灵运“池塘生春草”为“新”。但黄庭坚论诗并不主张“新”,因此这跟黄庭坚无关。又说:“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这是批评陈师道作诗时,闭门苦思。即把陈师道代表江西诗派,贬低陈师道即贬低江西诗派。钱先生又引元好问《杜诗学引》称“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朱弁《风月堂诗话》:“山谷以昆体工夫,到老杜浑成地步。”元好问“宁下涪翁拜”,可能就为了这点。所以他的诗里就称杜甫的古雅,李商隐的精纯,认为黄庭坚都不及。虽不及,但他“以昆体工夫,到老杜混成地步”,所用的工夫还是好的,所以还推重他吧。
这是一首豪气快意的小令,前两句先通过服饰、车马表明自己身居高位;接下来再正面抒发自己气吞山河的气势,以及辅佐帝王、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全曲写得气势非凡,一气贯通。
开篇两句呈现出一种华丽的贵胄之气和踌躇满志之态。“金鱼玉带罗襕扣”是从衣饰显示出其品阶,显然伯颜此时已身居高位,位列五候,甚是尊贵。他所佩戴的金鱼鱼符,所系的玉饰腰带,所穿衣服的扣子,无一不是达官贵人特有的佩饰,昭示着他们的门第身份和地位。
“皂盖朱幡列五候”,写的是其仪仗车饰,显示其位高权重。古代高官出行往往用黑色的车盖,红色的旗帜,即“皂盖朱幡”。元代并无裂地封侯之制,此处用“列五侯”来表明他身处高官显贵之列。
位高者权也重,对江山社稷自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山河判断在俺笔尖头”写的就是这层意思。疆域虽大,河山虽壮,却全在俺笔尖掌握。有一种站在河山之巅,俯瞰中华大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天下之大,舍我其谁的豪气。将河山之重与笔尖之轻相提并论,有举重若轻的洒脱与优游感。
“得意秋,分破帝王忧”的结句将作者的志得意满和豪气干云演绎到极致。据说作此小令之时,伯颜已率师攻破建康,与其他两路元军会师临安,南宋幼主已降。此时,正是伯颜建功立业的得意之秋。此句实际上是作者自明心志,建功立业并非是要图谋个人荣华,而是要为帝王分忧,其胸怀天下,高瞻远瞩的气魄令人感佩,难怪他病卒后,谥“忠武”。
这首小令朴实、飘逸,有豪迈之气,其中“山河判断在俺笔尖头”之句颇有宏大气象。前几句极言其“武”,英武和事功兼备。后面一句点题,表明其“忠”。
这首词借咏柳讽刺了隋炀帝的荒淫无度。
上片写隋炀帝锦帆龙舟下汴河,极尽铺张。
下片写其荒淫误国。“笙歌”句饶有韵味,将由繁盛转为破亡的历史教训,一笔端出,颇有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