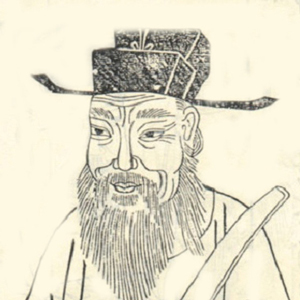在古典诗词中,以渔父为题材的作品,从楚辞《渔父》起,多不胜数。古代诗人常把渔夫视为隐者形象。一般写渔夫的作品多客观描绘其飘然物外、自得其乐,而钱起这首五古却写了“与渔者宿”,别出蹊径,饶有新趣。
诗的前六句写爱渔者的居住地。诗人漂游在外,到了蓝田溪渔者的住处,觉得找到了自己追寻的理想境地。本来就是“独游屡忘归”的,何况此时到了一个隐者栖息的地方,则更感到得其所哉。这里有清泉明月,有隐逸高士,境合于心,人合于情,自然更是心惬神怡了。诗人描写对蓝田溪的喜好,层层推进,“况此隐沦处”,意为更加“忘归”,继而以水清可以濯发,月明使人留恋,进一步说明隐沦处的美好。
最后以“更怜垂纶叟”,更爱那老渔翁,归结到愿和渔者同宿的期望上。隐处的好,就在于这里“清”、“明”、“静”,作者将这些意念以特有的景物予以编织,构成了一幅世外桃源的美好图景。
诗的中间四句写与渔者宿的乐趣。诗人与渔者宿,并不是因为旅途无处可栖,而是清夜长谈,得到了知音。谈论之中,渔者飘然物外的情怀,千里沧洲的乐趣,使自己心向往之。“白云心”,用陶潜《归去来辞》“云无心而出岫”意,就如柳宗元《渔翁》中写“岩上无心云相逐”以喻隐者之意一样。“沧洲趣”,即隐居水边之趣。沧洲,滨水的地方。古代常作为隐士的居处。诗人与渔者同宿,纵谈隐居之道,遁世之乐,不觉野火烧尽,东方破晓。可见两人通宵煮水烹茗,畅谈不休,其乐融融。
最后两句写与渔者不忍分别之情。诗人为此时分手如飞禽各栖其枝而叹息,不知何时再得相遇,惆怅不已。由此又将与渔者宿的感情推进一层。
古代诗词中写隐士多写不遇。隐士隐姓埋名,遁世避居,要写时往往“以影写竿”,如唐代贾岛的《访隐者不遇》,丘为的《寻西山隐者不遇》,陆畅的《送李山人归山》,宋代魏野的《寻隐者不遇》等等。
如要写相遇之人,多写渔者、樵者、耕者,而很少如钱起这样写与隐居的渔者同宿的。钱起这样写,增强了人们对隐者的生活与情志的真实感,同时从诗人吐露的与渔者同宿的投契、眷念上,表现了他的胸襟。
张谓的诗,不事刻意经营,常常浅白得有如说话,然而感情真挚,自然蕴藉,如这首诗,就具有一种淡妆的美。
开篇一联即扣紧题意,写洞庭秋色。“八月洞庭秋”,对景兴起,着重在点明时间。“潇湘水北流”,抒写眼前所见的空间景物,表面上没有惊人之语,却包孕了丰富的感情内涵:秋天本是令人善感多怀的季候,何况是家乡在北方的诗人面对洞庭之秋。湘江北去本是客观的自然现象,但多感的诗人联想到自己还不如江水,久久地滞留南方。因此,这两句是写景,也是抒情,引发了下面的怀人念远之意。颔联直抒胸臆,不事雕琢,然而却时间与空间交感,对仗工整而自然。“万里梦”,点空间,魂飞万里,极言乡关京国之遥远,此为虚写:“五更愁”,点时间,竟夕萦愁,极言客居他乡时忆念之殷深,此为实写。颈联宕开一笔,以正反夹写的句式进一步抒发自己的愁情:在乡愁的困扰下,翻开爱读的书籍已然无法自慰,登酒楼而醉饮或者可以忘忧。这些含意诗人并没有明白道出,但却使人于言外感知。同时,诗人连用了“不用”、“偏宜”这种具有否定与肯定意义的虚字斡旋其间,不仅使人情意态表达得更为深婉有致,而且使篇章开合动宕,令句法灵妙流动。登楼把酒,应该有友朋相对才是,然而现在却是诗人把酒独酌,即使是“上酒楼”,也无法解脱天涯寂寞之感,也无法了结一个“愁”字。于是,尾联就逼出“有怀”的正意,把自己的愁情写足写透。“故人京洛满”的热闹与诗人独处异乡的冷清形成鲜明对照。在章法上,“京洛满”和“水北流”相照,“同游”与“为客”相应,首尾环合,结体绵密。从全诗来看,没有秾丽的词藻和过多的渲染,信笔写来,皆成妙谛,流水行云,悠然隽永。
淡妆之美是诗美的一种。平易中见深远,朴素中见高华,它虽然不一定是诗美中的极致,但却是并不容易达到的美的境界,所以北宋诗人梅圣俞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扫除腻粉呈风骨,褪却红衣学淡妆,清雅中有风骨,素淡中出情韵,张谓这首诗,就是这方面的成功之作。
全词描述了离别前的忧伤、临别时的依依不舍,以及悬想别后友人归家与亲属团聚的情景。前面实写,后面虚写,多次转移时间和空间,逐层抒发离情别绪,在章法和布局方面颇具匠心。
上阕刻画客中庭院之萧瑟,为离愁作铺垫,可分两层。前六句为一层,以雨后寂寞萧条的庭院为背景,写别前的忧伤。莲花凋零了粉色的花瓣,桐树吹动着带绿的叶子,是初秋院中之景。竹篱边发光暗淡的萤虫,苔阶下鸣声凄切的蟋蟀,是秋夜庭前之物。篠墙,指竹墙。这四样景物,有昼景,有夜景;有植物,有动物;植物又有花、有叶,动物又有光、有声,配置匀整,而且从目见写到耳闻,从视觉写到听觉,造成一种冷清凄迷的意境,无限烦恼尽在其中。中间“暗雨乍歇”写天时,“抱影销魂”写人事。“还见”二字,更透露出一种无可奈何之感。何以如此,是因为即将送别友人。江淹《别赋》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这种离愁别绪,由于用了许多惹愁的景物层层烘染,便见得加倍的浓重。这六句词,使人俨然进入宋玉《九辩》的境界。
“送客”以下开始转入离别,是第二层。场景由庭院逐渐移至送别的水边。西去,表客行方向。重寻,表明在此送行已非一回。“问水面琵琶谁拨”,化用白居易《琵琶行》中“忽闻水上琵琶声”的诗句,而改为以“问”字领起的设问句,语简意深,余味悠长,极尽其缠绵情绪。接着,“最可惜、一片江山,总付与啼鴂”,则声情激越,境界阔远寄慨遥深。啼鴂,或作鹈鴂、鶗鴂,又名子规、杜鹃,此鸟“春分鸣则众芳生,秋分鸣则众芳歇”(《广韵》)。屈原《离骚》中有“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之句。这里也是借啼鴂的鸣声来表现众芳芜秽、山河改容的衰飒景象,衬托离情,极为沉痛感人。其中还隐微地寄托了词人的身世之感、家国之痛。飘泊江湖的迟暮之感,山河异色的忧愁之悲,都体现在这一凄迷阔远的境界之中。正是无限感慨都在虚处,意愈切而词愈微。
下阕写留客殷勤之意,也有两层意思。前六句承上,着重写惜别之情。“长恨”三句与柳永《雨霖铃》过片处“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有同工之妙。柳词以“更那堪”三字递进一层,此词则以“而今何事”的设问追进一步,以倾吐惜别的深情。然后再以“渚寒”三句景语来代替情语,这里又与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诗的“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的艺术手法相似,借淡烟寒水之中一叶行舟缥缈远去的景象,来表达送别者伫立江头,凝望着棹移人远的那种依依不舍的感情。这与周邦彦《兰陵王》“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首迨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有异曲同工之妙。周词是站在离别者回望送别者的角度来写,姜词是从送别者眼中离别者远处的情景,虽角度不同而各尽其妙。
最后六句写别后,用美好的设想来排遣双方的离愁别恨。文君即卓文君,借指胡的妻室。“倚竹”句借用杜甫《佳人》诗“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和李白《玉阶怨》诗“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中的妇女形象,以表现想象中胡妻等待丈夫归来的情景。“翠尊”三句亦化用李白同诗的后两句:“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描绘胡氏夫妇团聚的情景。点化前人诗句的艺术形象为自己所用,不着痕迹,尽得风流,这也是姜夔词的艺术特色之一。
这首词以清笔写浓愁,以健笔写深哀,故感情真切而不流于颓表,符合白石词中和的特色。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论说:“声情激越,笔力精健,而意味仍是和婉,哀而不伤,真词圣也。”细腻而有层次的抒情笔法,配合以移步换形的结构形式,也有助于形成那种清健空灵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