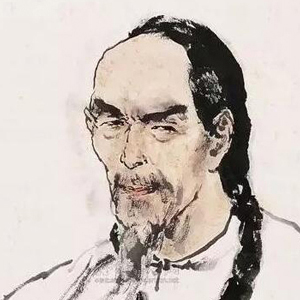此词里描写了沦陷区的荒凉景象和敌人的骄横残暴,抒发了反对议和的激昂情绪。
上阕,描写江淮区域宋金对峙的态势。“长淮”二字,指出当时的国境线,含有感慨之意。自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宋“与金国和议成,立盟书,约以淮水中流画疆”(《宋史·高宗纪》)。昔日曾是动脉的淮河,如今变成边境。这正如后来杨万里《初入淮河》诗所感叹的:“人到淮河意不佳”,“中流以北即天涯!”国境已收缩至此,只剩下半壁江山。极目千里淮河,南岸一线的防御无屏障可守,只是莽莽平野而已。江淮之间,征尘暗淡,霜风凄紧,更增战后的荒凉景象。
“黯销凝”一语,揭示出词人的壮怀,黯然神伤。追想当年靖康之变,二帝被掳,宋室南渡。谁实为之?天耶?人耶?语意分明而着以“殆”、“非”两字,便觉摇曳生姿。洙、泗二水经流的山东,是孔子当年讲学的地方,如今也为金人所占,这对于词人来说,不禁从内心深处激起震撼、痛苦和愤慨。自“隔水毡乡”直贯到歇拍,写隔岸金兵的活动。一水之隔,昔日耕稼之地,此时已变为游牧之乡。帐幕遍野,日夕吆喝着成群的牛羊回栏。“落日”句,语本于《诗经·王风·君子于役》,更应警觉的是,金兵的哨所纵横,防备严密。尤以猎火照野,凄厉的笳鼓可闻,令人惊心动魄。金人南下之心未死,国势仍是可危。
下阕,抒写复国的壮志难酬,朝廷当政者苟安于和议现状,中原人民空盼光复,词情更加悲壮。换头一段,词人倾诉自己空有杀敌的武器,只落得尘封虫蛀而无用武之地。时不,徒具雄心,却等闲虚度。绍兴三十一年的秋冬,孝祥闲居往来于宣城、芜湖间,闻采石大捷,曾在《水调歌头·和庞佑甫》一首词里写道:“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但到建康观察形势,仍感报国无门。所以“渺神京”以下一段,悲愤的词人把词笔犀利锋鋩直指偏安的小朝廷。汴京渺远,何时光复!所谓渺远,岂但指空间距离之遥远,更是指光复时间之渺茫。这不能不归罪于一味偷安的朝廷。“干羽方怀远”活用《尚书·大禹谟》“舞干羽于两阶”故事。据说舜大修礼乐,曾使远方的有苗族来归顺。词人借以辛辣地讽刺朝廷放弃失地,安于现状。所以下面一针见血揭穿说,自绍兴和议成后,每年派遣贺正旦、贺金主生辰的使者、交割岁币银绢的交币使以及有事交涉的国信使、祈请使等,充满道路,在金受尽屈辱,忠直之士,更有被扣留或被杀害的危险。即如使者至金,在礼节方面仍须居于下风。岳珂《桯史》记载:“……礼文之际,多可议者,而受书之仪特甚。逆亮(金主完颜亮)渝平,孝皇(宋孝宗)以奉亲之故,与雍(金世宗完颜雍)继定和好,虽易称叔侄为与国,而此仪尚因循未改,上(孝宗)常悔之。”这就是“若为情”——何以为情一句的事实背景,词人所以叹息痛恨者。“闻道”两句写金人统治下的父老同胞,年年盼望王师早日北伐收复失地。“翠葆霓旌”,即饰以鸟羽的车盖和彩旗,是皇帝的仪仗,这里借指宋帝车驾。词人的朋友范成大八年后使金,过故都汴京,有《州桥》一诗:“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曾在陕西前线战斗过的陆游,其《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一诗中也写道:“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皆可印证。这些爱国诗人、词人说到中原父老,真是同深感慨。作者举出中原人民向往故国,殷切盼望复国的事实,就更深刻地揭露偏安之局是多么违反人民意愿,更使人感到无比气愤的事。结尾三句顺势所至,更把出使者的心情写出来。孝祥伯父张邵于建炎三年使金,以不屈被拘留幽燕十五年。任何一位爱国者出使渡淮北去,就都要为中原大地的长期不能收复而激起满腔忠愤,为中原人民的年年伤心失望而倾泻出热泪。“使行人到此”一句,“行人”或解作路过之人,亦可通。北宋刘潜、李冠两首《六州歌头》,一咏项羽事,一咏唐玄宗、杨贵妃事,末皆用此句格。刘作曰“遣行入到此,追念痛伤情,胜负难凭”;李作曰“使行人到此,千古只伤歌,事往愁多”。孝祥此语大概亦袭自前人。
纵观全词,上阕又可各分为三小段,作者在章法上也颇费心思。宴会的地点在建康,词人唱出“长淮望断”,他不让听者停留在淮河为界的苦痛眼前现实,而且紧接着以“追想当年事”一语把大家的心绪推向北方更广大的被占区,加重其山河破碎之感。这时又突然以“隔水毡乡”提出警告,把众宾的注意力再引回到“胡儿打围涂塘北,烟火穹庐一江隔”(张孝祥《和沈教授子寿赋雪》诗句)的现实中来。一阕之内,波澜迭起。换头以后的写法又有变化。承上阕指明的危急形势,首述恢复无期、报国无门的失望;继斥朝廷的忍辱求和;最后指出连过往的人(包括赴金使者)见到中原遗老也同样悲愤。这样高歌慷慨,愈转愈深,不仅充分表达了词人的无限悲愤之情,更有力地激发起人们的爱国热情。据南宋无名氏《朝野遗记》说:“歌阕,魏公(张浚)为罢席而入”,可见其感人之深。
这首词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词人“扫开河洛之氛祲,荡洙泗之膻腥者,未尝一日而忘胸中”的爱国精神。正如词中所显示,熔铸了民族的与文化的、现实的与历史的、人民的与个人的因素,是一种极其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所以一旦倾吐为词,发抒忠义就有“如惊涛出壑”的气魄(南宋滕仲固跋郭应祥《笑笑词》语,据称于湖一传而得吴镒,再传而得郭)。同时,《六州歌头》篇幅长,格局阔大。多用三言、四言的短句,构成激越紧张的促节,声情激壮,正是词人抒发满腔爱国激情的极佳艺术形式。词中,把宋金双方的对峙局面,朝廷与人民之间的尖锐矛盾,加以鲜明对比。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宏观历史画卷,强有力地表达出人民的心声。就像杜甫诗历来被称为诗史一样,这首《六州歌头》,也完全可以被称为词史。
这首词亦见于冯延巳的《阳春集》。清人刘熙载说:“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艺概·词曲概》)在词的发展史上,宋初词风承南唐,没有太大的变化,而欧与冯俱仕至宰执,政治地位与文化素养基本相似。因此他们两人的词风大同小异,有些作品,往往混淆在一起。此词据李清照《临江仙》词序云:“欧阳公作《蝶恋花》,有‘深深深几许’之句,予酷爱之,用其语作‘庭院深深’数阕。”李清照去欧阳修未远,所云当不误。
此词写闺怨。词风深稳妙雅。所谓深者,就是含蓄蕴藉,婉曲幽深,耐人寻味。此词首句“深深深”三字,前人尝叹其用叠字之工;兹特拈出,用以说明全词特色之所在。不妨说这首词的景写得深,情写得深,意境也写得深。
词上阕以“庭院深深深几许”起句,点明女主人所处环境“庭院”,而三个“深”字的叠字运用更形象地描绘出女主人所处环境之“深幽”。这三个字不仅写出“庭院”之幽深更写出了女主人内心的幽深孤寂。词人紧接又用“杨柳”、“堆烟”、“帘幕”这些意象将女主人内心之凄之怨刻画的淋漓尽致。其中“堆”字尽道杨柳之密,烟雾之浓。试想女主人在庭院独上幕楼放眼遥望茂密的杨柳萦绕着浓浓的雾霭仿似一幅水墨画。奈何如此美景却寻不见丈夫的踪迹,眼前景物狠心地阻隔了她的视线,内心无端升起无限悲凉来。虚数“无重数”与“几许”相呼应,暗示阻隔视线的岂止是“杨柳”、“堆烟”、“帘幕”那么简单。女主人因何望夫?丈夫到哪里去了呢?既不当兵也不从商而是“玉勒雕鞍游冶处”。丈夫在外风流快活而自己却只能独上幕楼凝眉空望,叹息楼台之幕让自己看不见章台路。后两句点名女主人内心凄婉、空怨的原因。女主人明知丈夫在外风花雪夜,但内心还是怀有期盼,哪怕只看见丈夫离去的背影也好,奈何这点要求也难以满足,只得独自忍受着深院的冷漠寂寥。
下阕则是女主人内心世界引发的感伤。“雨横风狂三月暮”,其中“横”和“狂”直接点破女主人那异常不平的内心世界。三月的春风细雨原本极其温柔,然而这里雨不是“斜雨”而是“横雨”,风不是“煦风”而是“狂风”,原本美丽的“三月”却饱含着一份无情。“暮”字足见女主人等待之久,或许一天,或许一年,或许一辈子。多情的等待换来的却是无情的深深庭院里的不尽的黑夜。“夕阳无限好”,女主人已无意黄昏,一个“掩”诉尽她内心的凄凉。“无计留春住”看似“无计留春”实则是感叹女子容颜易逝。“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青春未逝况且如此,青春流逝那还有什么盼头呢?此情此景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一位独处深闺的女子日日期盼着良人,奈何良人却无意家中,成天风花雪夜在外头鬼混;日子一天天过去,自己的青春也一天天消逝,自己又凭什么期盼良人回心转意呢?内心油然升起无限寂寥、感伤、无奈之情来。女主人公最后只能寄情于“落红”,自己恰如那凋谢的落花一去不复返,再无人想起她那令人怜爱的容颜。“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泪即是为花也是为己,或许是花的残败触动了女子的心事,或许是女子自感身世怜花垂泪。“不语”则表现女主人内心孤寂无人理解的愁苦。“乱红飞过秋千去”更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感伤。
词中写了景,写了情,而景与情又是那样的融合无间,浑然天成,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意境。读此词,总的印象便是意境幽深,不徒名言警句而已。词人刻画意境也是有层次的。从环境来说,它是由外景到内景,以深邃的居室烘托深邃的感情,以灰暗凄惨的色彩渲染孤独伤感的心情。从时间来说,上片是写浓雾弥漫的早晨,下片是写风狂雨暴的黄昏,由早及晚,逐次打开人物的心扉。过片三句,近人俞平伯评日:“‘三月暮’点季节,‘风雨”点气候,‘黄昏’点时刻,三层渲染,才逼出‘无计’句来。”(《唐宋词选释》)暮春时节,风雨黄昏;闭门深坐,情尤怛恻。个中意境,仿佛是诗,但诗不能写其貌;是画,但画不能传其神;惟有通过这种婉曲的词笔才能恰到好处地勾画出来。尤其是结句,更臻于妙境:“一若关情,一若不关情,而情思举荡漾无边。”(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王国维认为这是一种“有我之境”。所谓“有我之境”,便是“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人间词话》)。也就是说,花儿含悲不语,反映了词中女子难言的苦痛;乱红飞过秋千,烘托了女子终鲜同情之侣、怅然若失的神态。而情思之绵邈,意境之深远,尤令人神往。
这首词抒发了作者羁旅的愁思和对妻子的思念。上阙首尾写景,中间穿插议论。秋景自然引发乡愁,‘‘庾肠”、“皤髻”等连续用典,悲叹年华已逝。下阙写妻子思夫,想像对方思念之苦。结尾“情到不堪言处,分付东流”更是悲苦之极。
上片落笔写景,首先点明季节。“木叶亭皋下”三句,写时近重阳,树叶纷纷飘落到平荡的水边地上,又是妇女为亲人捶打寒衣的深秋了。这种“捣衣”之声,最易引起闺中少妇对远方征人的痛苦思念。而远行之人也容易因此想到妻子在家为自己捣衣的情景,既感到痛苦又温暖。这里“木叶”“捣衣”连用,不仅写出了深秋特有的景色,为全词烘托出萧瑟凄清的背景,而且为下面的词意发展作了有力的铺垫。
“奈愁入庾肠,老侵潘鬓,谩簪黄菊,花也应羞。” 这数句又紧承起句,意思说,怎奈我愁绪萦绕心中,白发现于鬓角,再轻慢地把黄菊插在头发上,那菊花也该感到羞辱吧。词人由于忧伤,鬓衰将不胜簪,故云:“谩簪黄菊,花也应羞。”以此反衬出暮感的深沉、乡愁的浓烈。
“楚天晚,白苹烟尽处,红蓼水边头。”在写景中寓离别相思之意。心中既然充满乡愁暮感,所以不仅遥望楚天的晚空,一直望到水气缭绕的白苹尽头,一直望到水边开花的红蓼深处。“白苹”,水中浮草,因其随波漂流,容易引起游子产生离家漂泊的伤感。
词人是淮阳人,所以,遥望楚天,思乡之念便在不言中了;再加两点染,则把他乡愁之深烘托出来了。这里虽纯是写景,但景中含情,意在言外。
“芳草有情,夕阳无语,雁横南浦,人倚西楼。”数句紧承“白苹”“红蓼”两句而来,含着情意的芳草,默默无语的夕阳,横渡南面水滨的大雁,是词人所望到的,但却没有望到故乡,在这种望而不得的情况下,他只好倚着西楼心往神驰了。这几句写景,将词人遥望故乡而不得的执着深情又推进了一层,词意含蓄,画面完整,真所谓“物以情观,情以物见”了。“人倚西楼”点出游子登眺之处,交代了“楚天晚”至“雁横南浦”六句都是极目之所见;由所见而引起所感,因而所见之景物都似有了人的感情。
下片换头“玉容知安否?”点明所思之人,揭示了词旨所在,使上片所写种种情景明朗化。这句“玉容”,极言容貌之美如花似玉,这儿即指倚楼遥思的对象。“知安否?”曲尽对遥思对象的关切和挂念,由此而引起下面相思的倾诉、深情的抒发。
“香笺共锦字,两处悠悠。空恨碧云离合,青鸟沉浮”意谓书信和题诗,由于两地渺远而无法见寄,徒然地怨那晴云分离,使者隐没。“碧云”这里借以写对于闺中人的怀思。由于香笺锦字,两处悠悠,碧云已合而佳人未来,青鸟杳然而音书全无。词人于此以铺叙写法表达两地分居、不见来信的怅怨,愈加显出“知安否”所包含的深沉挂念的分量。
“向风前懊恼”四句,转以想象之笔,设想妻子思念自己时的痛苦情状。他想象妻子也许在风前月下,芳心懊恼,眉头紧皱,怎么也止不住那百无聊赖的愁思。写对方思念自己,正是为了表达自己对于妻子深挚的爱情与痛苦的思念。
“情到不堪言处,分付东流”用质语绾合全篇。相思至极,欲说还休;不是不想说,而是说了愈加愁苦,倒不如将此情交付给东流之水带去为好。毛滂《惜分飞》曾云:“今夜山深处,断魂分付潮回去。”构思、手法与此相同。
这首词艺术上的一个特点是用典极丰,而又不露痕迹,毫无堆砌罗列之感,显得贴切自然、浑然天成;另外全词六副对偶,也令人叫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