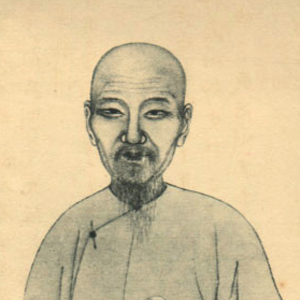“残灯风灭炉烟冷,相伴唯孤影。”起笔便是一副凄凉孤寂之境。夜风骤起,吹灭了摇曳的灯火,香炉里的烟灰早就凉透了。一阵风将房间里唯一的光明和温暖,不由分说地夺走了,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影子,伴着孤零零的词人。
“判教狼藉醉清樽,为问世间醒判是何人?”既然无人作伴,只有清酒陪伴自己。纳兰所说的“醒判”之人,便是屈原这般不随波逐流,英雄式的理想主义者。纳兰又何尝不是在以屈原自喻。身边小人对权势趋之若鹜,纳兰始终冷判以对,保持高洁之心,只是,这样一人对抗千军万马的日子,多么的孤单,多么的凄凉。
“难逢易散花问酒,饮罢空搔首。”纳兰心事无人知,只有友人顾贞观懂他,但是相聚之日不多,不能时常与纳兰互诉衷肠,饮酒作诗。纳兰不住地叹息,别离漫长,相逢苦短,知己已去,剩自己一人面对这早早散了的宴席。酒喝光了,只能对着满桌的空杯搔首长叹。
“闲愁总付醉来眠,只恐醒时依旧到樽前。”这句写得无限凄凉。既然闲愁萦怀,难以排遣,就让酒来麻醉它们吧,然后,再麻醉我自己,换得一时的安稳睡眠。可是醒来之后依然孑然一身,依然愁绪满怀、怕是又要到酒杯面前,喝得大醉一场。
全词表达了词人对友人顾贞观的怀念之情以及对当时身世的无奈,情真意切。
此诗咏汉文帝与贾谊,但与李商隐诗的着眼点不同,议论更大相径庭。李诗以小事而见大节,王诗则因大事而忽小节。王安石认为贾谊的政略,文帝基本都有采用,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官职的高低与否不重要;李商隐抱负难申,乃为贾谊悲,王安石得宋神宗宠遇,乃为贾谊喜,正是不同的遭际,才产生出不同的议论来。就诗歌艺术而言,此诗纯是议论,褒贬分明,对比强烈。
诗的前两句“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一写贾谊,一写文帝。诗中指贾谊的治国安民之方,这两句是反诘句,意为贾谊所献的“谋议”,大体上都能获得施行,所以说文帝并不轻视贾谊。以贾谊进言与文帝纳言相对照,承班固《汉书·贾谊传》中之“赞”词:“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与前人写贾谊怀才不遇之作唱反调。
后两句“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一写爵位高的“公卿”,一写君王。这两句也构成了一个反诘句,意为:自古以来,不知有多少达官贵人,尽管他们的官爵职位很高,但其言论都被君王废弃了。弦外之音是贾谊比那些达官贵人更为幸运。
此诗采用两个反诘句,寓答于反问之中,以贾谊的“谋议略施行”与身居高位的达官贵人“言尽废”相对照,以文帝采纳贾谊的“谋议”,古来君王废弃众多地位显赫的达官贵人的言论相对照,突出贾谊超群的才能与汉文帝的爱惜贤才。
此诗不像李商隐的《贾生》那般讽文帝悼贾生,反而赞文帝褒贾生。这是因为王安石受到宋神宗的殊遇,依托他推行新法,他也就有了新的体验,认为贾谊只是遭到周勃灌婴等人的谗毁而未能如愿以偿而已。从以上的比较中不难看出,李商隐与王安石的同题诗《贾生》,虽然都是咏贾谊,但各自的着眼点不同,笔法相异,主要在于两位诗人的思想有别,他们根据各自的思想对同一人物发表独特的见解,前者欲抑先扬,以古讽今,笔锋犀利而含蓄,后者褒贬分明,对比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