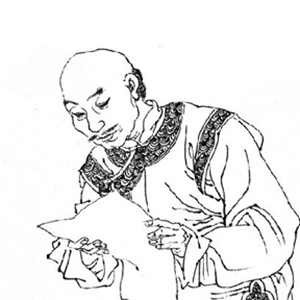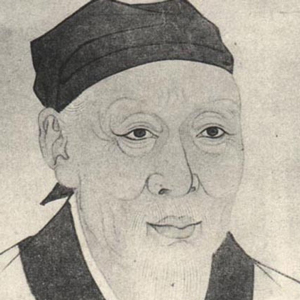被闻一多先生誉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宫体诗的自赎》)的《春江花月夜》,一千多年来使无数读者为之倾倒。一生仅留下两首诗的张若虚,也因这一首诗,“孤篇横绝,竟为大家”。
此诗沿用陈隋乐府旧题,运用富有生活气息的清丽之笔,以月为主体,以江为场景,描绘了一幅幽美邈远、惝恍迷离的春江月夜图,抒写了游子思妇真挚动人的离情别绪以及富有哲理意味的人生感慨,表现了一种迥绝的宇宙意识,创造了一个深沉、寥廓、宁静的境界。全诗共三十六句,每四句一换韵,通篇融诗情、画意、哲理为一体,意境空明,想象奇特,语言自然隽永,韵律宛转悠扬,洗净了六朝宫体的浓脂腻粉,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素有“孤篇盖全唐”之誉。
诗人入手擒题,一开篇便就题生发,勾勒出一幅春江月夜的壮丽画面:江潮连海,月共潮生。这里的“海”是虚指。江潮浩瀚无垠,仿佛和大海连在一起,气势宏伟。这时一轮明月随潮涌生,景象壮观。一个“生”字,就赋予了明月与潮水以活泼泼的生命。月光闪耀千万里之遥,哪一处春江不在明月朗照之中!江水曲曲弯弯地绕过花草遍生的春之原野,月色泻在花树上,像撒上了一层洁白的雪。诗人真可谓是丹青妙手,轻轻挥洒一笔,便点染出春江月夜中的奇异之“花”。同时,又巧妙地缴足了“春江花月夜”的题面。诗人对月光的观察极其精微:月光荡涤了世间万物的五光十色,将大千世界浸染成梦幻一样的银辉色。因而“流霜不觉飞”,“白沙看不见”,浑然只有皎洁明亮的月光存在。细腻的笔触,创造了一个神话般美妙的境界,使春江花月夜显得格外幽美恬静。这八句,由大到小,由远及近,笔墨逐渐凝聚在一轮孤月上了。
清明澄彻的天地宇宙,仿佛使人进入了一个纯净的世界,这就自然地引起了诗人的遐思冥想:“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诗人神思飞跃,但又紧紧联系着人生,探索着人生的哲理与宇宙的奥秘。这种探索,古人也已有之,如曹植《送应氏》:“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阮籍《咏怀》:“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等等,但诗的主题多半是感慨宇宙永恒,人生短暂。张若虚在此处却别开生面,他的思想没有陷入前人窠臼,而是翻出了新意:“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个人的生命是短暂即逝的,而人类的存在则是绵延久长的,因之“代代无穷已”的人生就和“年年只相似”的明月得以共存。这是诗人从大自然的美景中感受到的一种欣慰。诗人虽有对人生短暂的感伤,但并不是颓废与绝望,而是缘于对人生的追求与热爱。全诗的基调是“哀而不伤”,使我们得以聆听到初盛唐时代之音的回响。
“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这是紧承上一句的“只相似”而来的。人生代代相继,江月年年如此。一轮孤月徘徊中天,像是等待着什么人似的,却又永远不能如愿。月光下,只有大江急流,奔腾远去。随着江水的流动,诗篇遂生波澜,将诗情推向更深远的境界。江月有恨,流水无情,诗人自然地把笔触由上半篇的大自然景色转到了人生图象,引出下半篇男女相思的离愁别恨。
“白云”四句总写在春江花月夜中思妇与游子的两地思念之情。“白云”、“青枫浦”托物寓情。白云飘忽,象征“扁舟子”的行踪不定。“青枫浦”为地名,但“枫”“浦”在诗中又常用为感别的景物、处所。“谁家”“何处”二句互文见义,正因不止一家、一处有离愁别恨,诗人才提出这样的设问,一种相思,牵出两地离愁,一往一复,诗情荡漾,曲折有致。
以下“可怜”八句承“何处”句,写思妇对离人的怀念。然而诗人不直说思妇的悲和泪,而是用“月”来烘托她的怀念之情,悲泪自出。诗篇把“月”拟人化,“徘徊”二字极其传神:一是浮云游动,故光影明灭不定;二是月光怀着对思妇的怜悯之情,在楼上徘徊不忍去。它要和思妇作伴,为她解愁,因而把柔和的清辉洒在妆镜台上、玉户帘上、捣衣砧上。岂料思妇触景生情,反而思念尤甚。她想赶走这恼人的月色,可是月色“卷不去”,“拂还来”,真诚地依恋着她。这里“卷”和“拂”两个痴情的动作,生动地表现出思妇内心的愁怅和迷惘。月光引起的情思在深深地搅扰着她,此时此刻,月色不也照着远方的爱人吗?共望月光而无法相知,只好依托明月遥寄相思之情。望长空:鸿雁远飞,飞不出月的光影,飞也徒劳;看江面,鱼儿在深水里跃动,只是激起阵阵波纹,跃也无用。“尺素在鱼肠,寸心凭雁足”。向以传信为任的鱼雁,如今也无法传递音讯──该又凭添几重愁苦!
最后八句写游子,诗人用落花、流水、残月来烘托他的思归之情。“扁舟子”连做梦也念念归家──花落幽潭,春光将老,人还远隔天涯,情何以堪!江水流春,流去的不仅是自然的春天,也是游子的青春、幸福和憧憬。江潭落月,更衬托出他凄苦的寞寞之情。沉沉的海雾隐遮了落月;碣石、潇湘,天各一方,道路是多么遥远。“沉沉”二字加重地渲染了他的孤寂;“无限路”也就无限地加深了他的乡思。他思忖:在这美好的春江花月之夜,不知有几人能乘月归回自己的家乡!他那无着无落的离情,伴着残月之光,洒满在江边的树林之上……
“落月摇情满江树”,这结句的“摇情”──不绝如缕的思念之情,将月光之情,游子之情,诗人之情交织成一片,洒落在江树上,也洒落在读者心上,情韵袅袅,摇曳生姿,令人心醉神迷。
《春江花月夜》在思想与艺术上都超越了以前那些单纯模山范水的景物诗,抒儿女别情离绪的爱情诗。诗人将这些屡见不鲜的传统题材,注入了新的含义,融诗情、画意、哲理为一体,凭借对春江花月夜的描绘,尽情赞叹大自然的奇丽景色,讴歌人间纯洁的爱情,把对游子思妇的同情心扩大开来,与对人生哲理的追求、对宇宙奥秘的探索结合起来,从而汇成一种情、景、理水乳交溶的幽美而邈远的意境。诗人将深邃美丽的艺术世界特意隐藏在惝恍迷离的艺术氛围之中,整首诗篇仿佛笼罩在一片空灵而迷茫的月色里,吸引着读者去探寻其中美的真谛。
全诗紧扣春、江、花、月、夜的背景来写,而又以月为主体。“月”是诗中情景兼融之物,它跳动着诗人的脉搏,在全诗中犹如一条生命纽带,通贯上下,触处生神,诗情随着月轮的生落而起伏曲折。月在一夜之间经历了升起──高悬──西斜──落下的过程。在月的照耀下,江水、沙滩、天空、原野、枫树、花林、飞霜、白沙、扁舟、高楼、镜台、砧石、长飞的鸿雁、潜跃的鱼龙,不眠的思妇以及漂泊的游子,组成了完整的诗歌形象,展现出一幅充满人生哲理与生活情趣的画卷。这幅画卷在色调上是以淡寓浓,虽用水墨勾勒点染,但“墨分五彩”,从黑白相辅、虚实相生中显出绚烂多彩的艺术效果,宛如一幅淡雅的中国水墨画,体现出春江花月夜清幽的意境美。
诗的韵律节奏也饶有特色。诗人灌注在诗中的感情旋律极其悲慨激荡,但那旋律既不是哀丝豪竹,也不是急管繁弦,而是像小提琴奏出的小夜曲或梦幻曲,含蕴,隽永。诗的内在感情是那样热烈、深沉,看来却是自然的、平和的,犹如脉搏跳动那样有规律,有节奏,而诗的韵律也相应地扬抑回旋。全诗共三十六句,四句一换韵,共换九韵。又平声庚韵起首,中间为仄声霰韵、平声真韵、仄声纸韵、平声尤韵、灰韵、文韵、麻韵,最后以仄声遇韵结束。诗人把阳辙韵与阴辙韵交互杂沓,高低音相间,依次为洪亮(庚、霰、真)──细微级(纸)──柔和级(尤、灰)──洪亮级(文、麻)──细微级(遇)。全诗随着韵脚的转换变化,平仄的交错运用,一唱三叹,前呼后应,既回环反复,又层出不穷,音乐节奏感强烈而优美。这种语音与韵味的变化,又是切合着诗情的起伏,可谓声情与文情丝丝入扣,宛转谐美。
古代诗词中,以“游春”、“咏春”为主题的作品何止千百篇,但内容大多不外乎“伤春”、“怅春”。赵秉文的这首《青杏儿》不与前人雷同,风格清新,语句明白如话,本色天然。
上片首句:“风雨替花愁”,语句凝炼,一个“替”字,生动地表达出作者对花的关切之情。当暴风雨袭来的时候,娇嫩的花儿必将遭受风雨的摧残。多情的词人不免“替”花儿深深地担忧。“风雨罢,花也应休”,想来当肆虐的狂风暴雨过后,遍地残红,花期也该成为过去了吧。花开又花落,不由人不惜花,而那多情善感的赏花人、惜花人,也就在这花飞花谢、春去春来中白了少年头。所以,年年岁岁,岁岁年年,时光如流水,莫负春光啊,这也是“劝君莫惜花前醉”的缘故。词的上片写至此处,词人表达了几许怅惘悲伤之感。
然而,词人却不想用更多的悲凉、迟暮感来感染读者。笔调轻轻一转,“乘兴两三瓯”,下片意境立刻由沉闷、苦恼转向了明彻、欢快。“莫惜”深化为“乘兴”,揭示人们要积极开创美好的生活,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要尽情享受。两三盏薄酒,听江山清风,观山间明月,柳绿花红,莺飞草长,造物是这样的神奇,大自然是这样的美妙,做人应该“拣溪山好处追游”,得欢愉时且欢愉,莫要自寻烦恼。“但教有酒身无事,有花也好,无花也好,选甚春秋。”词的结尾表达只要胸襟豁达,有美酒相伴,无俗事缠身,有花也罢,无花也罢,春天永远常在,春光永远无限。
这首词上下片对比鲜明,语言通俗易懂,又不流于俗白,体现了作者的艺术修养和旷达的人生情怀。
这首诗描写了这样一幅场景:一位久居城里的官员,得空到乡间去放风游览,吃的是农家菜,住的是农家院,于是由衷地羡慕起田园生活来。
前四句写“赵叟”的生活环境,以及其高洁的品行与美好的生活情趣;中间四名描写赵叟日常生活,极富田园情趣;最后写此次宴饮的场面,呈现出一幅和谐闲适的田园生活的画面。全诗写得自然流畅,诗人在字里行间表现出的,都是对隐居生活的向往和对主人生活情趣的赞美。
首句“虽与人境接”,说明这位赵姓老人的家离城市并不远,可能就在郊区。虽然住的地方不是很偏远,但是“闭门成隐居”,过的就是闲静的田园生活。这两句诗颇有点“心远地自偏”的味道。接下来的二句,诗人对赵叟进行了赞美,谓赵叟能谈玄,有儒行。诗人先把主人比成庄子,又拿孔子来比喻,皆是称赞主人既有高洁的品行,又有美好的生活情趣。
“深巷斜晖静,闲门高柳疏”,写赵叟每日所见,深巷里的夕阳斜照之情景,营造出了静美的氛围。“荷锄修药圃,散帙曝农书”,写的是赵叟日常所为,侍弄田地,整理书籍,既有体力劳动,又有脑力劳动,悠闲而舒适,极富田园情趣。
接下来诗人笔锋一转,最后四句回到宴饮来,写此次宴饮的场面。“上客摇芳翰”,写“上客”的活动,体现了钦佩之情;“中厨馈野蔬”写主人的在准备饮食。最后两句则是一个长镜头,先是主人与朋友们在客厅里痛饮,然后镜头拉远,柴门出现了,柴门外的景色出现了,人物活动在优美的自然景色之中,呈现出一幅和谐闲适的田园生活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