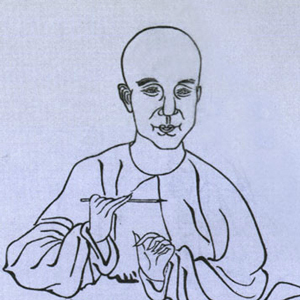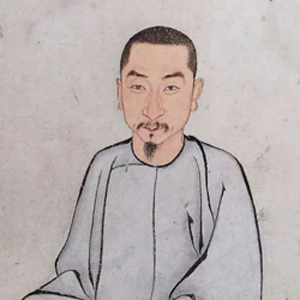在《周颂·访落》中,周成王诉说自己年幼,缺少治国经验,请求诸侯辅助,既陈实情,又表诚意。当然,只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对于诸侯,更需要的是施以震慑。诗中两提周武王(“昭考”“皇考”),两提遵循武王之道,震慑即由此施出。
参与朝庙的诸侯均是受武王之封而得爵位的。身受恩惠,当报以忠诚,这是道义上的震慑;武王虽逝,他所建立的国家机器(包括强大的军队)仍在,这是力量上的震慑。
最有力的震慑是诗中表达的遵循武王之道的决心。如果说“率时昭考”还嫌泛泛,“绍庭上下,陟降厥家”就十分具体了。武王在伐纣前所作准备有一条“立赏罚以记其功”(《史记·周本纪》)与诗中“上下”“陟降”相似,惟成王所处时局更为严峻,他所采取的措施也会更为严厉。舜即位后曾“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尚书·舜典》),这是成王可以效法,并可由辅佐他的周公实施的。
《周颂·访落》其实是一篇周王室决心巩固政权的宣言,是对武王之灵的宣誓,又是对诸侯的政策交代,真诚而不乏严厉,严厉而不失风度,周公也借此扯满了摄政的风帆。
诗的前两句描绘了春天的早晨嘉兴城外春风和畅,春水荡漾,春草繁茂的景象。“晓风催我挂帆行,绿涨春芜岸欲平。”首句的诗眼在一“催”字,是清晨湖上的晓风的催。这一句既点明了时间,与诗题呼应,也交代了诗人自己所处的地点。他此时身在船上也许刚刚迈出船舱,如果不是清凉沁人的晓风,还不会这么早就挂帆起航。“催”字把景物和人物的关系传达出来了。第二句写湖景,描写舟行所见。“绿”字下得极好,和“涨”字结合在一起,给人丰富的色彩想象和运动感,那碧色的湖水仿佛就在眼前漾动,晃人的眼睛。水色苍翠,原野才能与之一色,“平”字也才更好落实。用色彩词代替名物词是古典诗词最具表现力的手法之一,这里是一个典型例证。
后两句写天晴过后,片片油菜田冲击着诗人的乡情。“长水塘南三日雨,菜花香过秀州城。”这两句是全诗精粹所在。第三句承上启下,为末句作铺。诗人正由长水塘坐船到达嘉兴。路上春雨连绵,水势迅涨。可以想见雨过天晴之后,诗人从船舱中跨出来,那种新鲜、清爽的青春感受。这时他写下了最传神的一句,“菜花香过秀州城”。这一句全写感觉,然而容量也最大,写出了诗人对家乡最独特的那种感受。诗人没有写其他的鲜花,却把那带着泥土芳香的油菜花味突现出来。这花味把诗人浓厚的乡情全唤起来了,像醇酒一样令他陶醉其中。在一片菜花清香中诗人驶过了秀州城。这个“过”字既是船过,也是香过,更是情过,里面蕴含多少联想,引发出多少新的体验,足可令读者作无穷的想象和深思。
前两句,写的是风,是船,是春水、春草,却令读者感到,诗人心中也已晓风拂拂,风帆满满,春潮洋溢,碧草茸茸。后两句,使人想到朴素的民歌。歌手直抒胸臆,不加雕饰,如同童子直言,随口而出,歌声中充满了儿童一般的真诚与坦率,单纯稚拙而又有趣。
这首小令旨在寻梅。梅的品格历来为诗人所赞颂,特别是志在山林、对现实中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者,常以爱梅自娱,表现其高洁恬淡的品格。“寻”字是此曲的中心,全曲围绕何处寻、如何寻、寻到后又如何的线索,逐层描写。
起首三句写何处去寻,目标落在贺监与放翁住地,因为他们是高洁的隐居者,该处的梅又是人品似梅品者“亲自栽”的。
四、五、六三句承前三句补充说明鉴湖的梅梅品高于一般的梅,意为它“路近蓬莱”,蓬莱亦泛指仙境,它“远尘埃”,与龌龊的社会隔离。因此,作者心里总是记挂着去鉴湖寻梅,为尚未见到梅花而烦恼。
接下来两句是写如何寻。按照梅的特性去寻,“雪模糊小树莓苔”,梅是迎寒斗雪开放的,要到雪地里寻,“小树莓苔”言幽静的地方。早梅又名江梅,是生长在水滨的,要到水边去寻。“月朦胧”写梅花夜间开放,并与末句“昨夜一枝开”相呼应。
最后四句写寻到早梅后的喜悦,赶紧去买酒,对梅饮酒吟诗作曲。“猜,昨夜一枝开”是神来之笔,它不单是借典点明了这是早梅,更是为“寻”字增添分量。 他终于寻到了这迎寒风斗霜雪,最先开放在鉴湖水滨的品格高洁的早梅。寻梅的过程展现了诗人的爱好与情操,特别是不畏严寒、战风斗雪的精神。
本曲写得放达,风雅,流露出作者远离官场,走近自然的豁达胸襟。全曲情景相生,质朴清雅,体现作者豪放的气魄和宽阔的胸襟。
这是一首描摹南园景色、慨叹春暮花落的小诗。
前两句写花开。春回大地,南园百花竞放,艳丽多姿。“花枝草蔓眼中开”,这句说眼见南园花草繁茂可爱。“开”主要是对“花枝”而言的,而诗中“草蔓”二字告诉读者,随着春深,绿草绿叶渐渐多了。万紫千红,逐渐会被“绿肥红瘦”的景象代替。“小白长红越女腮”这句用了一个比喻形容花朵的娇艳。“小白长红”就是白少红多的意思,也就是偏于红的粉红色,与“越女腮”连文,即以美人粉红的脸蛋来比喻花瓣色泽的鲜嫩。“越女腮”是由此产生的联想,把娇艳的鲜花比作越地美女的面颊,赋予物以某种人的素质,从而显得格外精神。
后两句写花落。日中花开,眼前一片姹紫嫣红,真是美不胜收。可是好景不长,到了“日暮”,百花凋零,落红满地。“可怜”二字表达了诗人无限惋惜的深情。是惜花、惜春,也是自伤自悼。李贺当时不过二十来岁,正是年青有为的时期,却不为当局所重用,犹如花盛开时无人欣赏。想到红颜难久,容华易谢,不免悲从中来。
“落花不再春”,待到花残人老,就再也无法恢复旧日的容颜和生气。末句用拟人的手法写花落时身不由己的状态。“嫁与春风不用媒”,委身于春风,不须媒人作合,没有任何阻拦,好像两厢情愿。其实,花何尝愿意离开本枝,随风飘零,只为盛时已过,无力撑持,春风过处,便不由自主地坠落下来。这句的“嫁”字与第二句中的“越女腮”相映照,越发显得悲苦酸辛。当时盛开,颜色鲜丽,宛如西施故乡的美女。而今“出嫁”,已是花残“人老”,非复当时容颜,抚今忆昔,倍增怅惘。结句婉曲深沉,制造了浓烈的悲剧气氛。这首七言绝句,以赋笔为主,兼用比兴手法,清新委婉,风格别具,是不可多得的抒情佳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