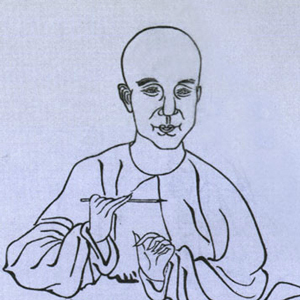这支有名的小令,是写思妇在春残雨细的时候,想到韶华易逝,游子未归,因而借酒浇愁,去打发那好天良夜。
曲的前两句,都不着痕迹地化用了唐人的诗句。“黄莺乱啼门外柳”,是写思妇,是从金昌绪的“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春怨》的诗意点染出来的。意思是说,她正想在那里“寻梦”,让那千种情思、万般缱绻在梦里得到满足,可那“不作美”的黄莺,好像故意为难似的在门外乱啼,使人不能成眠,无法在梦里补偿在现实生活中失去了的甜蜜。“雨细清明后”,是写行人,是思妇魂牵梦萦的对象,是从杜牧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清明》的句意中浓缩出来的。妙在思妇被黄莺唤起,不是埋怨行人误了归期,而是关心游子在阴雨泥泞的道路上黯然魂消的苦况,这就进一步深化了曲的意境。作者在这里引用唐人的诗句,有撮盐入水之妙。
“能消几日春”二句,是双承上面两句的曲意,即不但思妇禁受不起几番风雨,就是那天涯游子也同样受不了离愁的折磨了。这句话也是从辛弃疾的“要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的词意中点化出来,借春意阑珊来衬托自己的哀怨的怅然无限的相思,令人憔悴,令人瘦损,长此下去,如何是好呢?这里着一“又”字,说明这样的两地相思,已经不是破题儿第一遭了。这跟作者的“总是伤春,不似年时镜中人,瘦损!瘦损!”《庆宣和·春思》乃同一机杼。这支小曲之所以自然而不雕琢,典雅而不堆垛,正是作者博搜精粹,蓄之胸中,自然吐属不凡,下笔如有神助。
曲的头部和腹部,写得如此婉丽清新,结语须是愈加精彩,愈着精神,才能收到“余音绕梁”的艺术效果。所以“诗头曲尾”,古人是极为重视的。王骥德说:“末句更得一极俊语收之,方妙”《曲律·论尾声》。曲论家之所以不惮其烦,来总结曲的末句的艺术经验,说明它是关系到曲的成败的。这“梨花小窗人病酒”,就是俊语,就结得响亮,饶有余味。它既照应了前文的“清明后”和“几日春”,也概括了“相思瘦”的种种原因,又给读者留有充分想象的余地。因为梨花是春光已老的象征,她隔看小窗,看到梨花凋零,春事阑珊,而远人未归,闲愁无既,于是只好用酒来解除胸中的愁苦。病酒,就是伤了酒。读到这里,使人很容易联想到冯延巳的“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鹊踏枝·谁道闲情抛掷久》和李清照的“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凤凰台上忆吹箫·香冷金猊》的词意来。作者正是在这样的词情和意境的基础上,在曲尾对曲的整个意境作了很好的概括和创造,这才使人感到“言简而余味无穷”。
关于此诗,有一个传说故事:杜牧游湖州,识一民间女子,年十余岁。杜牧与其母相约过十年来娶,后十四年,杜牧始出为湖州刺史,女子已嫁人三年,生二子。杜牧感叹其事,故作此诗。这个传说不一定可靠,但此诗以叹花来寄托男女之情,是大致可以肯定的。它表现的是诗人在浪漫生活不如意时的一种惆怅懊丧之情。
全诗四句二十八字。诗人借寻春迟到,芳华已逝,花开花落、子满枝头,喻少女青春已过,含蓄委婉地抒发机缘已误,时不再来的惆怅之情。此诗通篇采用“比”的手法,形象生动,含蓄自然,耐人寻味。
首句的“春”犹下句的“芳”,指花。而开头一个“自”字富有感情色彩,把诗人那种自怨自艾,懊悔莫及的心情充分表达出来了。第二句写自解,表示对春暮花谢不用惆怅,也不必怨嗟。诗人明明在惆怅怨嗟,却偏说“不须惆怅”,明明是痛惜懊丧已极,却偏要自宽自慰,这在写法上是腾挪跌宕,在语意上是翻进一层,越发显出诗人惆怅失意之深,同时也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懊恼至极的情绪。
后两句写自然界的风风雨雨使鲜花凋零,红芳褪尽,绿叶成阴,结子满枝,果实累累,春天已经过去了。似乎只是纯客观地写花树的自然变化,其实蕴含着诗人深深惋惜的感情。
此诗主要用“比”的手法。通篇叙事赋物,即以比情抒怀,用自然界的花开花谢,绿树成阴子满枝,暗喻少女的妙龄已过,结婚生子。但这种比喻不是直露、生硬的,而是若即若离,婉曲含蓄的,即使不知道与此诗有关的故事,只把它当作别无寄托的咏物诗,也是出色的。隐喻手法的成功运用,又使此诗显得构思新颖巧妙,语意深曲蕴藉,耐人寻味。
王翰的《凉州词》是一首曾经打动过无数热血男儿心灵深处最柔弱部分的千古绝唱。诗人以饱蘸激情的笔触,用铿锵激越的音调,奇丽耀眼的词语,定下这开篇的第一句。
“葡萄美酒夜光杯”,犹如突然间拉开帷幕,在人们的眼前展现出五光十色、琳琅满目、酒香四溢的盛大筵席。这景象使人惊喜,使人兴奋,为全诗的抒情创造了气氛,定下了基调。
“欲饮琵琶马上催”是说正在大家准备畅饮之时,乐队也奏起了琵琶,更增添了欢快的气氛。但是这一句的最后一个“催”字却让后人产生了很多猜测,众口不一,有人说是催出发,但和后两句似乎难以贯通。有人解释为:催尽管催,饮还是照饮。这也不切合将士们豪放俊爽的精神状态。“马上”二字,往往又使人联想到“出发”,其实在西域胡人中,琵琶本来就是骑在马上弹奏的。“琵琶马上催”,应该是着意渲染一种欢快宴饮的场面。
诗的最末两句“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顺着前两句的诗意来看应当是写筵席上的畅饮和劝酒,这样理解的话,全诗无论是在诗意还是诗境上也就自然而然地融会贯通了,过去曾有人认为这两句“作旷达语,倍觉悲痛”。还有人说:“故作豪饮之词,然悲感已极”。话虽不同,但都离不开一个“悲”字。后来更有用低沉、悲凉、感伤、反战等等词语来概括这首诗的思想感情的,依据也是三四两句,特别是末句。“古来征战几人回”,显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清代施补华说这两句诗:“作悲伤语读便浅,作谐谑语读便妙,在学人领悟。”(《岘傭说诗》)这话对我们颇有启发。
之所以说“作悲伤语读便浅”,是因为它不是在宣扬战争的可怕,也不是表现对戎马生涯的厌恶,更不是对生命不保的哀叹。回过头去看看那欢宴的场面:耳听着阵阵欢快、激越的琵琶声,将士们真是兴致飞扬,你斟我酌,一阵痛饮之后,便醉意微微了。也许有人想放杯了吧,这时座中便有人高叫:怕什么,醉就醉吧,就是醉卧沙场,也请诸位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了。可见这三、四两句正是席间的劝酒之词,而并不是什么悲伤之情,它虽有几分“谐谑”,却也为尽情酣醉寻得了最具有环境和性格特征的“理由”。“醉卧沙场”,表现出来的不仅是豪放、开朗、兴奋的感情,而且还有着视死如归的勇气,这和豪华的筵席所显示的热烈气氛是一致的。
这是一个欢乐的盛宴,那场面和意境决不是一两个人在那儿浅斟低酌,借酒浇愁。它那明快的语言、跳动跌宕的节奏所反映出来的情绪是奔放的,狂热的;它展现出的是一种激动和向往的艺术魅力,这正是盛唐边塞诗的特色。
也有人认为全诗抒发的是反战的哀怨,所揭露的是自有战争以来生还者极少的悲惨事实,却出以豪迈旷达之笔,表现了一种视死如归的悲壮情绪,这就使人透过这种貌似豪放旷达的胸怀,更加看清了军人们心灵深处的忧伤与幻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