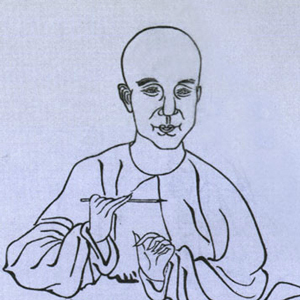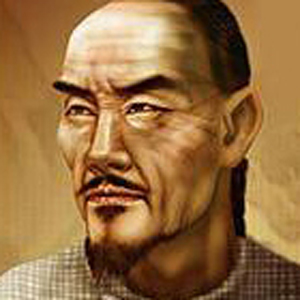一个女子痴心地渴望着,等待着重新见到那位朝思暮想的“君子”,她望穿秋水,等得心碎神伤。其实那位“君子”,恐怕压根儿已将她忘个罄尽。这首诗的内容实有揶揄嘲弄这位“君子”“二三其德”的况味。
全诗三章,章六句。首章用鹯鸟归林起兴,也兼有赋的成分。鸟倦飞而知返,还会回到自己的窝里,而人却忘了家,不想回来。这位女子望得情深意切。起首两句,从眼前景切入心中情,又是暮色苍茫的黄昏,仍瞅不到意中的“君子”,心底不免忧伤苦涩。再细细思量,越想越怕。她想:怎么办呵怎么办?那人怕已忘了我!不假雕琢,明白如话的质朴语言,表达出真挚感情,使人如闻其声,如窥其心,这是《诗经》语言艺术的一大特色。从“忘我实多”可以揣测他们间有过许许多多花间月下、山盟海誓的情事,忘得多也就负得深,这位“君子”实在是无情无义的负心汉。不过诗意表达得相当蕴藉。
“山有……隰有……”是《诗经》常出现的起兴成句,用以比况物各得其宜。上古时代先民物质生活尚不丰富,四望多见山峦坑谷正是历史的必然。那颙望着的女子瞥见晨风鸟箭样掠过飞入北林后,余下所见就是山坡上有茂密栎树和洼地里有树皮青白相间的梓榆。三章则换了两种树:棣和檖。之所以换,其主要作用怕是在于换韵脚。万物各得其所,独有自己无所适从,那份惆怅和凄凉可想而知,心里自然不痛快。三章诗在表达“忧心”上是层层递进的。“钦钦”形容忧而不忘;“靡乐”,不再有往事和现实的欢乐;“如醉”,如痴如醉精神恍惚。再发展下去,也许就要精神崩溃了。全诗各章感情的递进轨迹相当清晰和真实可信。
明朝万历年间,钱若赓就任临江府(今江西省清江县西临江镇)知府。
一天,一个乡下人拎了一只鹅到城里,为了办事方便,便将鹅寄存在一家旅店里。可是,当他办完事回来取鹅时,那店主竟耍赖说:“那群鹅是我养的,没你的鹅!”乡下人气愤与店主评理。但由于他没有文化,笨嘴拙舌的,辩不过伶牙俐齿的店主,只好跑到衙门去击鼓告状。
知府钱若赓细心听了乡下人的申述,立即命令手下人将店里的4只鹅全部取来,分关四处,每处配给一张纸、一支毛笔、一方砚台,说是让这些鹅招供各自属于谁。
鹅又怎么能自己招供?真是天大的笑话。城里的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都十分好奇地前来观看,连府中差役对钱若赓这种独特的审案方式也感到惊异和纳闷,无不替他捏了一把汗。
钱若赓似乎对案子漫不经心,刚布置完毕,就若无其事地用餐去了。过了一会儿,他派人出来探问;“鹅招供了没有?”
不久,钱若赓步出内室,亲自下堂巡视分关着的鹅,他看过以政,微笑着颔首捋须,自言自语:“嗯,好,好,它们已经招供啦。”差役们望过去,只见4只鹅除各自拉了些屎外,纸笔砚台丝毫未动。他们真的不知道钱知府卖的什么“关子”。突然,钱知府伸手指向其中的一只鹅,语气肯定地说道:“这只就是那乡下人的!”
钱若赓确实说对了。
钱若赓并不认识乡下人的鹅,他的判断是如何作出来的呢?原来,他是位富有生活经验的官吏。他知道,乡下的鹅吃的是野草,粪便是清淡的;城里的鹅吃的是谷子,粪便呈现黄色。要确定鹅的主人是乡下的还是城里的,只要查看一下鹅粪便一清二楚。
钱若赓把自己断案的依据讲出政,那个贪婪而又狡猾的店主顿时脸色煞白,连忙磕头谢罪。
戴名世是位史学家,他很得了司马迁《史记》笔法中那种神气逸韵的影响,他的文章结构既严谨,而行文又富于变化,莫窥行止,意蕴深远,即使在书信中也一样。
这篇散文开篇先交代作书目的,是要余生约僧人犁支来核实桂王政权的一些史料,却以自己无缘相见说起。犁支原是永历帝时的宦官,曾与人言及在桂王身边时的一些见闻,作者立即载笔以往,却未得见面,只好请余生记录下这些回忆并寄给自己,以之与多方访求才购得的《滇黔纪闻》一书对照比较,发现有不少出入,于是才写了这封信。文字虽不多,却将有关过程写得层次迭转而又清晰如画。
文章的第二段,阐叙编写南明史的意义。戴名世所处的年代,是清王朝已经大致稳固了它的统治,而同时又依旧严酷镇压汉族人民反清活动的时期,是否承认南明历史,实质上是否承认清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问题。作者认为南明政权的历史意义并不低于蜀汉和崖州的南宋政权。但由于严酷的文字禁锢,除山野遗民中可能会留下一些极简略的记载外,载于文字的史料实在太少,且又散于遗民隐士中极难寻得,何况这有限的载记还未能刊刻成书,乏于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随着坚持抗清的遗民旧臣相继而亡,南明政权的史实也必将很快湮没无闻,“岂不可叹也哉!”
文章第三段接上写搜集南明史料的种种艰难及自己的抱负。他公然称明祚为三百年,感叹“终明之末三百年无史”,已有的一些记载明史的书又“缺略不详,毁誉失实”。有感于世无司马迁、班固那样的史学家,于是慨然以修明史为己任。但自己一生又穷困潦倒,根本无力来搜集史料。再者,明亡之前的史书都未修成,就更不用说记载南明历史的史书了。翰林院虽曾广购旧书,但虑及自身安危,不但地方长官汰去涉及明清之际史实的著作,老百姓也不敢交出。这种情况下,要修一部完整的明史,实在是难乎其难了。文章至此,自然地便折回到作书的主旨上来,所以第四部分重申自己志愿与决心,强调自己游历少、闻见寡、交游不广,于修史极为不利,因而希望余生能召犁支来“面议其事”,情辞恳切,委婉动人。又回护照应了前文,包裹得十分严密。
文章层层推进,环环相扣,愈入愈深。而又首尾圆合,显得极有法度。这些特点也影响及于语言表达,如第一段叙两份史料的异同,笫二段叙修明史的意义,第三段叙面临的种种困难,都层次迭转、条理清晰又简洁明了、气韵生动,极富节奏感。更加善用曲笔,如“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如“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等等,都用貌似乎和之语,极深刻地揭露了清王朝文字狱的酷烈。
全诗两章,每章四句,均以“鹑之奔奔”与“鹊之强强”起兴,极言禽兽尚有固定的配偶,而诗中男主人公的行为可谓腐朽堕落、禽兽不如,枉为“兄”“君”。全诗两章只有“兄”“君”两字不重复,虽然诗人不敢不以之为“兄”、以之为“君”,貌似温柔敦厚,实则拈出“兄”“君”两字,无异于对男主人公进行口诛笔伐,畅快直切、鞭辟入里。
此诗作者可能是一位女子,她唾弃那被她尊重,却品德败坏的男人“鹑鹊之不若”。意思是鹑鹊尚知居则常匹,飞则相随的道理。而这位被她尊敬的男人,却败坏纲常,乱伦无道,肆意妄为,是一个禽兽不如的东西。而她却一直把他当作兄长、君子,岂知他并非谦谦善良之人,长而不尊,令她感到非常痛心。于是,她一怒之下,做诗斥之,以舒其愤。此诗的主旨应该立足于“女斥男”的根本之上。
全诗以比兴手法,告诫人们鹑鹊尚知居有常匹,飞有常偶,可诗中的“无良”之人,反不如禽兽,而作者还错把他当作君子一样的兄长。作者据此,将“无良”之人与禽兽对待爱情、婚姻的感情与态度,构成了一种强劲的反比之势,加强了诗歌的批判力量。
全诗虽然只有两章八句,并没有直接对男主人公的形象进行任何客观的描写,却能使其形象非常鲜明而且突出。这根源于诗歌文本所构筑出的剧烈而又异常强大的情感落差,此种落差来源于人与禽兽对待异性配偶的不同态度,这种态度的不同造成了这种巨大而有悬殊的逆向对比关系。从而使男主人公的恶劣形象直接迎面袭来,令人不寒而栗却又厌恶透顶。
诗歌上下两章前两句完全一样,只是位置发生了改变,却能给人造成一种回环与交错的感觉。每章后两句,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避免了反复咏唱时容易引起的单调的感觉。这对这种重章叠句的诗歌来说,应该是《诗经·国风》中的一种重要的艺术策略。